
我是乾宝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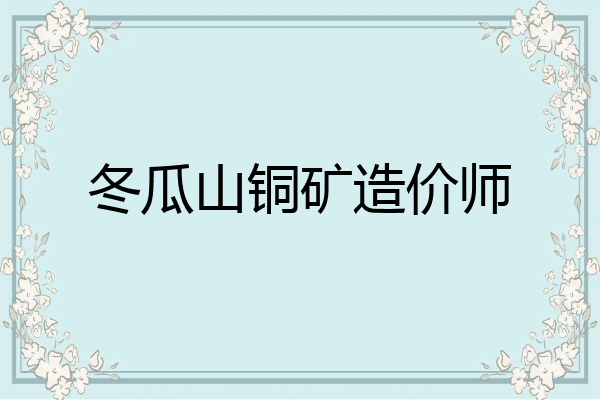

jiajia1994
狮子山铜矿(区),包括东西狮子山、老鸦岭、大团山和冬瓜山等一批大、中型隐伏(盲)矿床组成的矿床群,累计探明铜金属储量已逾150万吨,占铜陵地区铜储量的60%,是铜陵有色金属公司产铜的重要矿区之一。矿区位于铜陵市东偏南直距7公里,属铜陵市狮子山区管辖。市区有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和沿江铜陵港,市内公共汽车与狮子山相通,交通极为方便。矿区所处地质构造部位为大通-顺安复向斜中次一级青山背斜东段的轴部和东南翼。狮子山和大团山矿床赋存在下三叠统以碳酸盐岩为主的岩层中,老鸦岭主矿体赋存在上二叠统大隆组底部岩层中,其中、上部的次要矿体向深部延伸,形成了主要成矿围岩自上二叠统至下三叠统的碳酸盐岩、碎屑岩及其不同岩性层间裂隙、地层分界面;同熔型钙碱性中酸性岩和区域东西向深断裂复合了北北东向、北东向、南北向、北西向多种构造,控制了岩浆和矿床(体)的就位,实质上狮子山铜矿成矿模式是以热液脉型、夕卡岩型、层控夕卡岩及斑岩型子模式组合的模式——“多位一体”(多层楼)模式。诸矿床的矿石类型较为相似,以含铜夕卡岩型和含铜硫化物型为主,含铜角砾岩在狮子山矿床中出现,含铜蛇纹石岩型和含铜硬石膏岩型在冬瓜山矿床中出现。矿石铜平均品位在01%—60%范围内。诸矿床的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条件较好。狮子山铜矿床于1966年由铜陵有色金属公司狮子山铜矿建成投产以来,又开拓了老鸦岭铜矿床,大团山铜矿床1995年投产,冬瓜山铜矿床1993年提交勘探报告,现在北京有色设计总院正在进行设计,准备探采结合,以扩大矿山开拓规模。狮子山矿开采规模已由800—1000吨/日扩大到日产2000吨。本区已成为铜陵有色金属公司重要的原料基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狮子山地区的乡镇企业像雨后春笋,采掘浅而富的铜矿,不仅支持了铜矿事业发展,而且为脱贫致富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矿区古采坑、老窿、废石堆和炼渣分布广泛,自包村后山到沙子堡一线最为密集,炼渣大量堆积于大铜塘、冬瓜山等地,表明采、冶历史悠久,盛况非凡,但始于何时,无确切记载。据铜陵县志记载:“狮子山原名铜精山,……齐梁时置冶炼铜于此”,传闻,矿区东侧的木鱼山曾掘出古冰铜,考古定为西周—东周年间,可见采冶年代之久远。但其产量如何,何时衰竭无据可查。区内地质调查工作大致始于本世纪,从1931至1949年不断有地质工作者前来调查。最早的有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孙健初等,曾在鸡冠山测制1∶5万地形地质图1幅,对该区的铁矿做过较详尽的叙述;另外,谢家荣、孟宪民亦曾来本区进行地质、矿产调查研究,为在该区寻找矿产资源,积累了宝贵资料;1947年,谢家荣又根据铜官山铁帽下有铜的经验,专门来此检查,并做了以下工作:①提出该区有大面积的含铜夕卡岩;②对矿产地质做了较深入研究,测制了地质图;③做了有10万吨铜储量的乐观估计;④发现了罕见的铜白钨矿矿物;⑤提出了进一步工作建议。以上工作为以后的狮子山铜矿地质勘查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华东工业部矿产勘测处,分别派张兆瑾和刘宗琦及赵宗溥等来狮子山、铜官山一带进行铜矿地质调查。张兆瑾、刘宗琦完成了铜官山和鸡冠山—狮子山两处矿床地质详测任务,赵宗溥写了一份报告,对矿区地质、矿产提出了自己的认识。1952年,三二一队杨庆如、董南庭、沈永和、段承敬等填制了7平方公里的1∶2500地形地质图1幅,同时做了同比例尺的物探详查。1953年,杨庆如、方云波做进一步检查,圈出铜矿远景地段,指出今后重点应解决夕卡岩中铜的价值问题,首先应把注意力转向含铜夕卡岩,并提出钻探和硐探的建议。由于当时受国外夕卡岩型无大矿的影响,将该区准备进一步勘查的计划搁浅,三二一队由江南调往江北勘查,该区地质勘查工作中辍。(1)狮子山铜矿东、西狮子山矿床 东、西狮子山矿床是狮子山铜矿区发现、勘查最早的重要矿床之一。1956年6月,华东地质局组建了扬子江普查队(即三七四队)来狮子山地区普查,该队地质技术负责人李锡之和苏联专家耶果洛夫等,选择该区有远景的矿带和物探异常布置普查钻孔19个,在大铜塘至西狮子山长约1500米的夕卡岩带上发现了铜矿化,并在西狮子山施工的9号孔中,于孔深150米处见到了隐伏铜矿体,肯定了西狮子山矿段的找矿远景,并指出东狮子山有进一步工作的价值,从而揭开了狮子山矿区普查勘探工作的序幕。但由于当时施工的钻孔太分散,对西狮子山已发现的矿体形态、产状、规模也未做进一步的深入了解。1957年2月,华东地质局指示三二一队来本区继续做详查,三二一队派张启址、刘学圭等到狮子山,和扬子江队办了交接手续。当时由杨澄祥代理技术负责人近半年,之后,狮子山矿区在三二一队总工程师常印佛的组织领导下继续勘查,经过1957—1959年两年工作,证实东、西狮子山两个矿床均为有工业价值的铜矿床,并相继转入勘探。狮子山铜矿矿山采矿准备工作于1958年第一次上马,后因1959—1961年的3年调整,矿山采矿工作暂时下马,特别是1960年春到1961年秋找煤、铁的任务较紧,勘探区内大批勘查力量调去搞煤、铁,对狮子山铜矿的勘探形成了时做时停的半停顿状态,直至1961年秋才逐渐恢复初勘。1962年正式进入详细勘探,在以钻探为主追索圈定矿体的同时,并配合坑道验证,证实狮子山矿床主矿体形态呈似层状和透镜体;矿体最长50米,一般长150—200米,厚度8—12米。东狮子山矿体铜平均品位为23%,西狮子山矿体铜平均品位为17%,全区总的平均品位为20%。1963年勘探工作全部结束,同年12月,在以队长苏波、书记谈德明、总工程师常印佛等组成的狮子山铜矿床报告编写委员会领导下,由常印佛主持、参加并组织周作祯、黄广球、阎如燧、陈训雄、孙悦鹏、黄许陈、张兆丰、汪德镛、范奎斌、李孟珠、杨成兴、侯生秀、胡焕德、刘兆连等二三十名工程技术人员共同编写了《安徽铜陵狮子山铜矿床最终地质勘探报告》。先后投入钻探工作量15万米,总投资约529万元。1964年7月24日全国储委批准探明铜储量73万吨。其中:西狮子山铜金属储量04万吨,东狮子山铜金属储量69万吨。矿山采掘业于1966年投产,是铜陵冶炼基地的重点矿山之一。(2)狮子山铜矿老鸦岭矿床 老鸦岭矿床位于西狮子山矿床西南处,与东、西狮子山矿床毗邻。矿床发现过程比较简单,勘查进程较快。1949年,赵宗溥在狮子山矿区调查所写的一份报告中讲老鸦岭地表有矿点。现在的老鸦岭矿床是深部的全隐伏矿床,不是赵讲的地表矿点。1963年,普查分队在进行铜陵幅1∶5万区调的同时,开展了一项水化学找矿工作,在整理水化学成果中,反映老鸦岭西侧有铜的化探异常,提供了找矿信息。1966年初,省地质局副局长郭珍、总工程师严坤元等,在青阳审查省地质局三二一队1966年地质设计时,认为三二一队后备勘探基地紧张,矿点检查安排少了,提出要给普查分队增加一些矿点检查任务。根据省地质局意见,去汇报设计的三二一队副队长李勇、队代理技术负责人周作祯、分队技术负责人黄广球和刘学圭,在研究增加矿点检查任务时,着重讨论了老鸦岭矿点。认为1962年在开展狮子山外围填图工作时,周作祯和狮子山填图组的杨澄祥、张慎昭、蒋介狄等到过老鸦岭,当时曾对老鸦岭西坡的凹坑是不是古采坑遗迹就产生过疑问。以后普查分队又发现有水化学异常,结合该区位于背斜轴部以及地质构造、蚀变情况和矿化特征等,认为成矿条件是不错的;经过讨论,就在那个会上,决定给普查分队增加一个老鸦岭矿点检查项目。回队后由普查分队王乙长组织安排周全兴、杨关照等开展地表检查。经过半年的检查,确证老鸦岭西坡有古采迹存在,并在施工的槽、井工程底部发现了致密块状的原生铜矿体(层)。同年10月,三二一队决定由狮子山工区(原一分队)以地表矿化和浅井中见到的矿体(层)为依据,部署钻孔验证,从而发现了深部全隐伏矿体。它的发现显示了狮子山矿区找矿思路的一个转折性认识——层位控制矿体。后经广大地质技术人员反复研究对比,认识到老鸦岭主矿体赋存的层位是上二叠统大隆组底部,钻孔所揭示的矿体,基本上在这一部位,所以,老鸦岭主矿体的形态简单、呈似层状,并随岩层变化而变化,随岩层褶皱而褶皱。主矿体长1117米,平均厚度81米,铜平均品位为60%,(全区平均品位为04%)。说明狮子山矿区的矿床成因类型不仅有接触带夕卡岩型,还有层位控制这一成矿特点,从而丰富了矿床学的成因理论,进一步扩大地质工作者的找矿视野。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对老鸦岭矿床中见到的小矿体(如T-3和Q-1),也得到合理解释,认为实际上是分布在下三叠统层位中和下二叠统栖霞组层位中的矿体,为以后进一步普查找矿提供了有力的依据。1967年开始,增开钻机,进行了普查—详查—勘探三阶段的连续勘查,于1970年10月,由队革委会组织编写、提交了老鸦岭铜矿勘探报告。1973年2月又对11线以南的矿体进行了补充勘探,勘探结束后,由刘学圭、陈达源等人于1974年12月又编写提交了一份新的《老鸦岭铜矿床补充勘探报告》。两次总共完成1∶2000地形地质测量96平方公里,投入钻探工作量95万米、探槽2509立方米。1976年11月15日经省地质局批准,探明铜金属储量88万吨、伴生金374吨、银70吨、硒90吨、硫10万吨。(3)、狮子山铜矿大团山矿床 大团山铜矿位于老鸦岭铜矿的东北、西狮子山与老鸦岭之间,为老鸦岭矿床第11勘探线、标高在负500米以上的浅部见到的上三叠统矿体向深部延伸部分。是狮子山矿区继东、西狮子山矿床、老鸦岭矿床之后发现的又一个中型以上的铜矿床。1967年10月—1968年8月,为寻找“西狮子山式”夕卡岩铜矿,曾在大团山施工3个普查孔,未发现工业矿体而结束野外工作,编有《狮子铜矿区大团山铜矿点普查找矿小结》。1969年11月,三二一队在勘探老鸦岭铜矿床时发现了赋存于三叠系小凉亭组底部的铜矿体,当时只控制了浅部。1970年10月,全面开展了大团山铜矿的普查,于1973年2月结束野外工作,初步了解了矿床基本地质特征、控矿因素以及矿体大致分布范围,并求得铜地质储量68万吨,编有《狮子山矿区大团山铜矿床普查评价报告》。1978年4月到1981年6月进行初步勘探,以100×100米以及100—150米×80—150米勘探网度求得铜金属储量38万吨,编写了《安徽铜陵狮子山矿区大团山矿床初步勘探报告》。铜陵有色金属公司狮子山铜矿,自1966年建成投产以来,已开拓了东、西狮子山和老鸦岭三个矿床,现有生产矿山保有储量严重不足;大团山铜矿床的发现和勘查,作为狮子山矿的接替矿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应铜陵有色金属公司多次要求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的规划安排,经省地矿局研究,并经地质矿产部同意,1984年3月省地矿局给三二一队下达了《关于进行铜陵大团山、冬瓜山铜矿床勘探的通知》;同时,矿山为了开采大团山铜矿,开拓井巷已作了前期准备,现有的混合井井简已下延至负390米,在负200米中段开凿一个盲井,从负200至负700米中段与老鸦岭坑道采掘系统衔接起来,作为大团山矿床深部的坑道采掘系统。1986年4月—1990年7月,大团山矿床结束野外勘探工作。勘探证明,大团山主矿体长830米,呈透镜状、似层状产出,平均厚度21米,全区铜平均品位为02%。从普查到勘探共施工钻探10万米,其中地质探矿孔79万米,专门水文孔1897米,制图孔1165米,抽水试验10层/8孔。1990年7月由省地矿局三二一队总工程师诸骥、副总工程师兼矿区技术负责人杨志佳和报告主编人张慎昭等编写提交了《安徽省铜陵狮子山矿区大团山铜矿床勘探报告》。1990年12月29日安徽省矿产储量委员会审查批准探明铜金属储量38万吨、伴生金685吨、伴生银86吨。勘查总投资70万元,勘探成本为每吨铜金属储量约74元。(4)狮子山铜矿冬瓜山矿床狮子山矿区原来有个冬瓜山矿点,指的是铜塘边上的冬瓜山地表小矿点,现在的冬瓜山矿床是与上述矿点不同的深部全隐伏的冬瓜山大矿床。老鸦岭矿床被发现后,省地质局三二一队常印佛根据狮子山矿区多层位控矿的特点,在1969年和刘元玺研究进一步扩大找矿问题,商定以位于老鸦岭北部的一个钻孔(即198孔)中见到大隆组底部主矿层为依据,将198孔继续加深500多米,以探求铜陵(乃至沿江)地区最有利的容矿层位——石炭系,因钻孔进入闪长岩体于孔深36米处被迫停孔,虽未达到目的,却是一次有意义的探索。这个孔即为现在冬瓜山矿床南缘外的边界孔。以后唐永成、刘学圭等亦提出在青山背斜轴部隆起部位打深孔了解黄龙—船山组赋矿情况的建议。后来发现了大团山三叠系底部含铜夕卡岩矿层,进一步证实了狮子山矿区多层位控矿的规律,更增加了向深部探索石炭系层位的共识和决心。1974—1975年,在酝酿选点和决策上项目时,董庆山、陈达源、汪德镛、黄许陈、杨志佳、蒋耀明等做出了积极努力,指导、编制、修改了普查工作设计,并认真组织了实施,终于在1976年4月,当设计的6311孔施工到880米时见到了石炭系中赋存的铜(硫、铁)矿体,厚度达50米。同年,又布钻孔2个,均在同一层位见到了同一矿体,确定了冬瓜山矿床的远景,从而使狮子山矿区深部找矿获得突破。由此可见,冬瓜山铜矿床的发现,是经过长时间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多次探索、反复实践的结果。深部矿体发现后,紧接着开展扩大规模的追索和详查工作。随后即以200×100—200米的网度对这层矿体进行追索控制,工业部门得知这一找矿成果后,提出了与大团山矿同时加速勘探的要求。1983年省地矿局指出:“根据工业部门的要求,冬瓜山的34—75线的详查应作为重点,并于1984年第一季度提交详查报告”。据此,于1983年9月结束了冬瓜山矿床野外施工,转入报告编写。在省地矿局三二一队总工程师刘宗权的领导下,由刘大生、刘仲山、胡富娥等于1985年6月编写了《安徽铜陵狮子山矿田冬瓜山铜矿床详细普查地质报告》,1986年10月27日省地矿局审查批准了报告中获得的铜金属储量70万吨、共生硫铁矿石储量7356万吨,折标矿39万吨。根据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地质矿产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的联合发文,以及1991年元月22日,地矿部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在北京就冬瓜山铜矿勘探方案进行协商,并通过《关于冬瓜山铜矿床勘探方案意见》的会议纪要,在肯定冬瓜山铜矿床可以勘探的前提下,考虑到主矿体规模巨大,长1810米,平均视厚度24米,全区铜平均品位为01%,为尽快地给矿山生产部门提供资料,确定了以整体勘探、分段实施的最佳方案。首期勘探34—58线之间区段(现正在此区段进行勘探工作),1993年提交该区段的勘探报告;后期勘探58—75线之间区段,野外工作结束后一年提交《冬瓜山铜矿床勘探报告》。两区段各占总储量的50%左右,冬瓜山矿床勘探成果获地矿部地质找矿一等奖和科技进步奖。狮子山矿区铜矿规模的不断扩大,除因矿区本身具备了特殊的成矿地质条件外,还有以下几点成功的经验:①以矿区广泛分布的夕卡岩体、矿化、铁帽、古采坑、古炼渣为依据,坚持“就矿找矿”;②运用夕卡岩型铜矿接触交代成矿普遍规律,研究狮子山矿区以中、下三叠统层状矿体为主的成矿地质特征,寻找层位相同或类似层位的层状矿体;③重视基础地质研究,分析矿区最有利成矿部位,寻找、发现了位于背斜轴部上二叠统大隆组的层控矿床(体);④以铜官山铜矿富集层位——中、上石炭统黄龙、船山组和新发现的老鸦岭层控矿床(体)储矿层位为依据,预测、勘查发现了最理想的中、上石炭统黄龙、船山组层控矿床(体)。总结整个勘查工作过程和经验,是以地质理论为基础,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成功模式为导向,以勘查成果为依据,不断推动矿产地质勘查,使勘查成果不断扩大,从而建立和完善了狮子山矿区、乃至铜陵地区“多层楼层控夕卡岩型铜矿床”成矿模式。

等等等二爷de22
铜是人类使用最早的金属材料之一。据考古学家认定,新石器时代后期,人类就开始使用“红铜”(自然铜),并被称为“铜石并用时代”;之后,为青铜器时代。我国应用铜金属的时代很早,《史记·孝武本纪》记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在湖北发现了商代中期,距今约3000多年的铜器。甘肃武威县皇娘娘台遗址和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的红铜器定为公元前2000~2500年,同时与红铜器一起出土的还有青铜器,说明这时已进入青铜器时代。新疆伊犁地区尼勒克县城南的奴拉赛和圆头山两处开采辉铜矿古遗址中的支护木架和石斧经碳同位素测定为距今2300~2100年。我国自古以来铜一直是民用的主要金属材料之一,直到解放前的许多朝代的货币都是用铜合金制作成的。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很少进行铜矿地质勘查工作。仅有几个不定期开采的、产量很少的铜矿山,如安徽铜陵铜官山铜矿、云南东川铜矿等。因此,几乎没有探明的铜矿储量。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地质工作的开展,才开始有计划、有组织的铜矿地质勘查工作。半个世纪以来,铜矿地质勘查工作从未间断过。通过广大地质职工的努力,找到并探明了大量铜矿,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一、铜矿床勘查工作发展的三个时期我国铜矿床勘查工作在新中国建立时从发展老矿山开始,到现在运用现代地矿理论和各种高科技综合方法找铜,这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大体可概括为三个时期。发展老矿山,扩大远景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了大规模建设,因而需要各种大量铜矿资源,但当时资源情况不清,地质资料很少,要开展铜矿地质工作最快捷的办法是从几个已有的老铜矿山入手。当时首选了铜官山、东川和白银厂开展勘查。1951年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组织对铜官山老庙基山铜矿进行钻探。1952年地质部成立后,又组成321地质队对铜官山铜矿进一步勘查,首次探明铜金属储量26万吨,同时发现了狮子山含铜夕卡岩。但由于受当时国外夕卡岩型矿床无大矿的影响,找夕卡岩型铜矿工作搁浅。直到1956年华东地质局组建成扬子江普查队(374队)到狮子山普查,才在西狮子山见到隐伏的夕卡岩型铜矿,还指出了东狮子山有进一步工作的价值。1957年,321队接替374队继续工作,证实东西狮子山均为工业铜矿床。以后对外围的普查不断有新的发现,1965年发现了老鸦岭中型铜矿床,以后找到大团山等多个铜矿床。使铜官山地区探明的铜储量大增,于是在铜官山建成我国华东的重要铜矿生产基地。东川铜矿床是一个地处边远的小矿床,1951年对它开展勘查工作,很快取得了成效。1953年起相继发现了汤丹铜矿、稀矿山铜矿、滥泥坪、小水井等多个铜矿床,到1957年末,东川铜矿床累计探明铜储量达210万吨,成为我国西南一个铜矿基地。1950年,宋叔和先生对甘肃省白银厂开采铁矿时,见有铁帽,推测深部可能有铜,随即向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提出进一步开展工作。1951年组队上山,找到了折腰山和火焰山铜矿,当即展开工作,于1956年底结束折腰山、火焰山和铜厂沟等三个矿区勘探工作,提交铜金属储量86万吨,还发现了另一个大型矿床——小铁山铜多金属矿。白银厂成为我国西北的一个重要的铜矿基地。类似的情况还有中条山铜矿床,1952年对垣曲铜矿峪铜矿点开展调查工作,在我国首次认定了铜矿峪矿床为细脉浸染型(后称为斑岩型铜矿)铜矿。于1954年调集2000余名职工,进行大规模勘查工作。到1956年提交了探明铜金属储量达167万吨的勘探报告,形成了华北一个新的重要铜矿基地。4个原来不大或者仅为矿点的老矿山的重新认识和勘查,后来都扩大或肯定了其开发远景,成了我国重要的铜矿生产基地。发动群众报矿,就矿找矿时期1953年,中国开始执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地质工作提出的要求中明确“鼓励群众报矿”。从1953年起,地质部开展了群众报矿,广泛发动农牧民为主的群众找矿报矿,到1958年由于大炼钢铁,群众找矿报矿达到了空前规模。当时估计发现各种矿点、矿化点达20万处。这为后来的普查找矿提供了大量有用信息。我国惟一达世界级规模的甘肃金昌市金川铜镍矿和我国最大的斑岩型铜矿——西藏玉龙斑岩铜矿,就是根据群众报矿信息而发现的。青海玛沁德尔尼大型铜钴矿也是根据群众报矿发现的。没有群众报矿线索,像玉龙、德尔尼这样位于海拔4000多米,人迹罕至之处的矿,当时单凭专业地质队伍一时是难以走到和发现的。50年代后期根据群众报矿线索或矿床(点)就矿找矿发现了许多铜矿。到“二五”末(1962年),经过勘查上平衡表的铜储量猛增到1100多万吨。这和当时群众报矿和就矿找矿有密切关系。这种活动持续到70年代后期,根据这些线索,还发现了相当多的具工业价值的铜矿床。总结成矿规律,运用地矿理论指导找矿时期这方面的铜矿工作,是从长江中下游地区首先开始的。长江中下游从50年代开始铜矿普查勘探工作后,大量铜矿床被发现。从湖北大冶起,沿江而下经过江西、安徽、江苏直到上海,这一地带开始作为国家铜铁矿普查勘探的最重要地区。对长江中下游地区铜矿为主的矿床一般地就矿找矿已不易解决问题,而对该区成矿规律等的认识日渐深化,同时找矿的难度则与日俱增,于是进入了总结成矿规律,运用地矿理论来指导找矿的阶段。冬瓜山大型铜矿的发现是第一份丰厚的回报。铜陵狮子山接触交代型铜矿床成矿既有岩体与围岩接触带的控矿,又明显受岩层层位的控制。后来又发现了老鸦岭和大团山铜矿床,具有相似的控矿因素。当时地质队内以常印佛先生为代表的地质专家们反复研究和论证了区内石炭系黄龙—船山组的成矿条件后,认为这个层位分布的地区,即使隐伏地下也可能含矿。于是选择了冬瓜山西南约240m处进行探查,于1975年9月开始钻探,1976年4月见到了黄龙—船山组层位的铜矿,接着又施钻两个都见到了同一层位和同一类型的富铜矿,进一步的勘查结果,冬瓜山铜矿提交了铜金属储量93万吨。这一埋深近千米的全隐伏大富铜矿的发现,不仅在长江中下游找铜矿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证实了科学的预测,而且对地区的成矿规律的认识也是一个飞跃,使普查找矿工作迈进了一个新阶段。1979年下半年,湖北鄂东地质队薛迪康等在完成鄂东南地区1∶10万铁、铜、硫成矿预测成果的基础上,选择铜录山—冯家山铁铜矿田进行1∶1万成矿预测,总结矿田成矿规律,以矿田成矿模型为基础,按照“岩体前缘区,构造复合带,灰岩存在处”的找矿模式,对各种标志分析、类比,预测鸡冠嘴NNE向断裂破碎带在—500~—800m可能出现矿体。1981年11月,钻孔见到了厚达78m的全隐伏铜矿,取得了突破。最后探明为铜金属储量76万吨,共生金28t,硫铁矿石631万吨的大型金铜矿。福建紫金山地区地质工作始于1960年,进行过1∶20万区调、化探扫面、重砂测量以及地面槽井等工作,多次进进出出,没有取得重要进展。到1983年认定是金矿,但还未作出评价。1985年局总工石礼炎等认真仔细综合研究了紫金山地区的全部已有地质资料,认识到紫金山广泛发育有隐爆角砾岩,有大面积蚀变,还有多处铁帽,肯定了紫金山地区属于与次火山岩有关的矿化类型,推断深部有成铜远景。于是进一步加强工作和对新资料的综合分析研究,终于于1987年打到了隐伏的以蓝辉铜矿为主的大型斑岩型铜矿。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各地勘单位和有关研究部门都加强了铜矿床的研究,深入开展成矿规律、成矿条件和找矿标志的研究和总结。原地质矿产部正式部署了总结区域成矿规律,开展中大比例尺成矿预测,用以指导普查找矿工作。经过综合研究全国成矿条件后,将全国划出若干有找矿前景的远景区(片),固体矿产的勘查工作有重点地部署在片区上。同时强调运用综合手段找矿,区(调)、地(质)、物(探)、化(探)、遥(感)五统一部署工作。鉴于铜矿的找矿工作难度大大超过其他矿种,总结规律,应用地矿理论指导,进行预测和应用综合方法找矿就特别显得尤为重要。这样做的结果是陆续发现了一批铜矿,如湖北大冶的鸡冠嘴、桃花嘴大型金铜矿、新疆哈密黄山和黄山东铜镍矿、哈巴河阿舍勒大型海相火山气液型铜锌矿等。二、坚持不懈地勘查铜矿床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的铜铁原材料,而我国已探明的铜铁矿储量有限,因此,从50年代起“富铁富铜”一直作为地质勘查工作的重点。每年铜矿地质勘查工作的地勘费和工作量都占相当大的比重,从而每年都有新的铜矿床发现,相应地探明了一定的铜储量。根据可统计数据,历年对铜矿地质勘查工作的投资、使用的岩心钻探工作量和探明铜储量的增长情况如表1-1。表1-1 铜矿床勘查费、岩心钻探工作量和新增铜储量表 Table 1-1 Table showing exploration cost,core drilling footage and progressively increased reserves of copper metal注:比例数为以“一五”探明储量数为100%,各时期探明储量相当于“一五”的百分数。据统计,到1996年底,我国铜矿床地质勘查工作共投入地勘费25亿元,占固体矿产勘查工作总投入的24%,使用岩心钻探工作量约1379万米,占固体矿产岩心钻探总工作量的09%,最多一年为1977年,当年铜矿床勘查施钻达3万米。三、对我国铜矿床类型认识的发展前已述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铜矿床勘查工作是从几个已知矿床(矿点)的调查和评价起步的。在对它们的远景予以肯定并进入系统勘查后,对它们的成因类型也有了较深的认识,并且根据这些认识,在地质条件相似的邻近地区又陆续找到一些同类型的新矿床。但是当时对我国总的地质情况和成矿规律的知识还很肤浅,对我国铜矿类型的了解还很局限,因此对哪些铜矿类型在我国最有潜力,应该是主攻方向,哪些地区最有成矿远景,需要重点部署工作,还不是心中有数,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外经验的影响,存在着盲目性。例如,我国最早开始勘查的夕卡岩型(接触交代型)铜矿,由于当时受到国外对这类矿床消极认识的影响,在铜官山铜矿勘查之后,没有继续加大沿长江中下游各省具类似成矿条件地区工作的力度,至使该区铜矿工作一度徘徊不前。进入6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建设遇到巨大困难,迫切需要交通条件好,靠近已有工业基地的富铜资源,才促使我们重新重视长江中下游一带夕卡岩型铜矿床的工作。经过60年代以后持续30余年的不懈努力,终于确立了这种类型富铜矿在我国的特殊重要意义。对这种类型富铜矿的成矿规律也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并在其成矿理论上有了一批水平很高的著作成果问世。例如斑岩型铜矿床,在1954年探明了中条山铜矿峪斑岩铜矿床的大量铜矿储量后,在全国范围内激励起找寻这类铜矿的热潮。1956年发现了江西德兴斑岩铜矿,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矿点。但是由于我国这类矿床的次生富集作用不发育,缺少高品位的次生富集带,原生矿石较贫,在当时我国采冶技术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贫矿一时难以利用,因此找寻斑岩铜矿的热情开始低落。进入60年代随着板块构造学说的兴起,对斑岩铜矿成矿规律的进一步阐明和在世界范围内勘查斑岩铜矿热潮的启发下,原地质部1979年在江西德兴召开了斑岩铜矿工作现场会,推动了在全国有利地区找寻斑岩铜矿的高潮,发现并评价出一批斑岩铜矿,如西藏玉龙等世界级斑岩铜矿的勘查,就是最好的例证。到80年代初,我国斑岩铜矿的探明储量已远远超过其他类型而在我国居首位。而且经过实践已对我国斑岩型铜矿的成矿条件,成矿有利地区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工作的主动性更增强了。除了上述两个类型铜矿的实例外,对我国已发现和勘查过的其他铜矿类型在我国铜矿资源中不同重要性,及其成矿条件和找矿潜力的了解也更深化了。这样就使我国铜矿勘查工作能建立在目标明确的基础上,大大减少了盲目性。当然,地质工作还在发展中,新的铜矿类型还可能在勘查中被发现,已知的铜矿类型的认识还可能加深甚至发生改变,因此还需要在工作中继续加深对国内外各类型铜矿的研究,以求使我们的认识符合客观实际,进一步克服铜矿勘查工作中的盲目性,增强自觉性。四、铜矿床的开发利用从50年代的铜官山、中条山、东川和白银厂等几个老矿山开始建成为我国重要的铜矿基地起,随着新的铜矿床的不断发现和铜矿储量的扩大,新的铜矿山也陆续建成。我国铜的年产量平均以8%的增长率不断增加。根据“我国铜矿资源对2010年国民经济建设保证程度论证报告”资料,我国铜矿探明储量约有44%已被建设开发利用,共涉及矿区300多处,其中包括大中型矿床78处。如江西德兴铜厂铜矿、铅山县永平铜矿、湖北大冶县铜录山铜矿、甘肃白银市白银厂铜矿、金昌市金川铜镍矿、山西垣曲县铜矿峪铜矿、云南东川市东川铜矿等大型矿和一批中型矿;约有12%的探明储量可供建设利用但尚未被开采利用,其中大中型矿床13个,如江西九江县城门山、安徽铜陵市冬瓜山、江西德兴银山九区以及四川会理县拉拉厂和黑龙江嫩江县多宝山等大型矿床;约有32%的铜储量仅在规划考虑之中,共有269处产地,其中大中型矿床20处。这些矿床有的是位置偏远,目前交通不便,如青海玛沁德尔尼大型铜钴矿、兴海县铜峪沟大型铜矿等;有的铜品位低,如内蒙新巴尔虎右旗乌奴克吐山大型斑岩铜矿,铜储量有126万吨,但铜平均品位46%;广东曲江县大宝山大型铜多金属矿,铜矿体之上盖有几千万吨铁矿,影响了铜矿的近期开采;福建上杭县紫金山铜矿上部盖有几十吨金矿,先要开采金,铜只能延缓开发。诸如此类困难因素有客观的,也有人为的,致使大量探明铜储量不能马上建设利用。另外,还有目前暂难利用的铜金属储量约占探明总储量的11%多(包括大中型矿床24处),主要原因是矿石铜品位太低,选冶性能差,或外部建设或开采条件太差等。
优质职业资格证问答知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