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时何处
《墨西哥人》的主人公利威拉是个孤儿,他有一段很悲惨的遭遇。然而,小说在开头并没有花费笔墨介绍主人公的身世,而是直接让他进入行动,通过他的动作、言语、表情以及周围人对他的评论,把他的生动形象逐步展现在读者面前。杰克·伦敦没有采用一般的方法来“解释”。而是运用了我们在电影镜头里所常见的“切出”、“切入”手法,把小说主人公从“委员会”一下于带到轰动全场的拳击比赛场中。读者这才拨开迷雾,豁然开朗。原来,利威拉的父母都是忠诚的墨西哥革命者,在一次大屠杀中,双双惨死在狄亚士独裁政权的屠刀下。利威技侥幸得以脱身。跑到洛杉矶,为了糊口,便“到训练场里给别人当工具”,逐渐练就了他拳击的技巧。自从加入“委员会”后,“他才为钱去斗争。才发现这种钱容易捞”,不断用自己血汗挣来的钱捐献给革命。父母的惨死给利威拉幼小的心灵投下了巨大的阴影,过度的悲哀早已转化成强烈的复仇愿望。然而,残酷无情的现实又迫使他不得不把复仇的愿望深深埋藏于心底。这独特的个人道遇和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便铸造出这独特的利威拉的“冷’和“狠”。诚然,“冷”和“狠”既是利威拉的外表特征,又是他独具的坚韧、顽强、冷静个性的注解。这一点在拳击比赛场面中,显示得尤为充分。 拳击比赛是这篇小说的高潮。作者用了全文三分之二的篇幅来细致描述这场紧张激烈的争斗,目的并非单纯追求情节的生动,主要还是为了深化主人公的形象。进一步挖掘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作者十分懂得,“对比”和“映衬”是突现主人公性格特征的重要途径。因此,他先用对比手法写出利威拉和他的对手——拳王丹尼之间的种种悬殊,以造成丹尼稳操胜券的印象:一个是那样高大魁梧、威名显赫的拳场名将,观众对他的出场就欢呼了足足五分钟;另一个则是默默无闻的墨西哥“黑小子”,在观众眼里,“他不过是牵来让硕大的丹尼亲手宰割的羔羊”。然后,通过前几个回合的比赛,仍然写丹尼的锐不可当,“他的拳头好象转得飞快”,利威拉则被他打得晕头转向,险险乎败下阵来。及至最后,“利威捡的左拳突然向他右面死命一击,好象把他从半空中打了下来”,整个战局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最后几个回合的搏斗中,作者又多次描写丹尼的老奸巨猾、疯狂反扑,都是一一从反面衬托利威垃沉着、机智、勇猛顽强的性格。 小说的艺术特色在于几乎没有写人物的语言,而主要是通过人物的眼神和行动来刻划主人公外表沉默,内心火热,顽强、英勇胜于常人的性格。利威拉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时刻反映在他那双“充满深刻的仇恨”,“发出冷冷的寒光”的眼睛里。为了革命,他默默地甘当烧火、擦地板的清扫夫,他出色地完成了南下任务,他半夜里用拳赛后誉伤的,肿胀的手指在排字。作者还别具匠心地把人物性格放在紧张、残酷、揪人心肺的拳击比赛中来表现。他的坚毅,他的镇静,他那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他那感人至深的崇高的内心世界,在这场殊死搏斗中,被揭示得非常充分。作者挥洒自如,以满腔的革命激情,给读者塑造了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墨西哥青年革命者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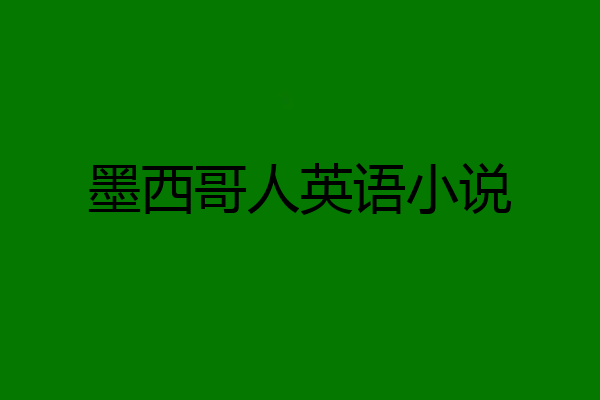

傻大明白
是杰克·凯鲁亚克创作于1957年的小说《on the road》?
《在路上》是凯鲁亚克的自传性代表作,小说主人公萨尔为了追求个性,与迪安、玛丽卢等几个年轻男女沿途搭车或开车,几次横越美国大陆,最终到了墨西哥,一路上他们狂喝滥饮,吸大麻,玩女人,高谈东方禅宗,走累了就挡道拦车,夜宿村落,从纽约游荡到旧金山,最后作鸟兽散……《在路上》1957年一经问世即令舆论哗然,毁誉参半。但不可否认的是,此书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被公认为20世纪60年代嬉皮士运动的经典。
杰克·凯鲁亚克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古老的纺织工业城镇洛威尔,他的父母亲是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的法国移民,直到六岁,凯鲁亚克才开始学习英语。凯鲁亚克的父母都是罗马天主教徒,父亲列奥·凯鲁亚克开了一家印刷厂,足以维持全家生计。凯鲁亚克排行老三,是家中最小的男孩,享受着平静而幸福的童年。四岁时,比他大五岁的哥哥杰拉德因病死去,凯鲁亚克对此印象极深。在他看来,杰拉德天资聪颖,对小动物尤其有怜悯之情,却被死神无情地带走了。家庭的宗教信仰及哥哥的过早夭折,使凯鲁亚克从小便相信再生来世,他后来笃信佛教可追溯到此事。
凯鲁亚克自幼生性腼腆,但却喜欢运动(骑马、棒球、足球),热衷于阅读文学作品。从中学起他便养成了随身携带笔记本的习惯,记录下周围的人和事——家人、朋友、邻居的日常谈话、广播节目、电影人物口中新奇的语言。他阅读广泛,从《哈佛文学经典》的英、法、俄、德、美国作家到当代作家的作品,例如海明威等。文学典故和街头下层人民的日常口语是凯鲁亚克作品中的两大特色,前者显然得益于他自幼对世界名著的酷爱与熟悉。
青年学生萨尔为追求个性自由,与狄安(以卡萨迪为原型)、玛丽露等一伙男女开车横穿全美,一路狂喝滥饮,耽迷酒色,流浪吸毒,性放纵,在经过精疲力竭的漫长放荡后,开始笃信东方禅宗,感悟到生命的意义。小说主人公及其伙伴沿途搭车或开车,几次横越美国大陆,最终到了墨西哥。
《在路上》体现了作者主张的即兴式自发性写作技巧,并广泛涉及美国社会一文化习俗,都给理解和翻译带来很大困难。
小说的核心人物是迪安,没有他就没有在路上的一切,在他的带动下,萨尔等人找个借口就上路了,他们搭车赶路,结识陌生人,放纵性情,随心所欲,在聚众旅行的狂欢中,几乎没有道德底限,即使落魄如乞丐,但只要“在路上”就是惬意的,萨尔曾经由衷地感叹:“啊,美好、温暖的夜晚,月光如水,搂着你的姑娘,喝喝酒,说说话,啐啐唾沫,简直是天上人间!”在这种混乱、亢奋而筋疲力尽的得过且过的状态背后,《在路上》的主题远没有它的语言那样轻快。书中的人物不停地穿梭于公路与城市之间,每一段行程都有那么多人在路上,孤独的、忧郁的、快乐的、麻木的……纽约、丹佛、旧金山……城市只是符号,是路上歇息片刻的驿站,每当他们抵达一个地点,却发现梦想仍然在远方,于是只有继续前进。
这是一本注定属于年轻人的书。作者曾经借书中迪安之口对萨尔发问:“……你的道路是什么,老兄?——乖孩子的路,疯子的路,五彩的路,浪荡子的路,任何的路。到底在什么地方、给什么人,怎么走呢?”我想这也正是对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提问,它以无与伦比的诱惑吸引着无数人上路,如今,“在路上”已经成为一种追逐精神自由飞扬的符号,它穿越了几代人,具有了普遍意义。背起行囊激动地上路,探求不可预知的旅途,似乎就可以“掌握开启通向神秘的种种可能和多姿多彩的历练本身之门”,“在路上”更像是一种自我标榜的仪式。
与《在路上》的迪安那伙人所不同的是,今天中国的年轻人相对理性,“垮掉的一代”是颓废地流浪着,今天中国的年轻人是极度渴望自由 ,他们从小受到的束缚比较多,所以虽然渴望自由精神,敢于蔑视传统,颠覆经典,恶搞名人,但实际上,大多数人并不敢冲破生活,也没有像书中的年轻人那样似乎逾越了大部分法律和道德界限。但对于一代又一代喜欢《在路上》的读者来说,凯鲁亚克表达出了大多数人心中的异化、不安和不满,因此这本书已经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种人生“想象的理想状态和醒悟的自由感觉”。
写到最后,我不由得想起这样一个情景,1995年暑假,我在塔里木盆地边缘的一间小客栈里遇到一位从北京来的女大学生,她正眯着近视眼在胡杨树下读书,书本封面上的名字赫然就是《在路上》,后来大家很快成了朋友,也许就是因为我口袋里也装了同样的一本书。
《在路上》是杰克·凯鲁亚克的第二部小说,在极度的时尚使人们的注意力变得支离破碎,敏感性变得迟钝薄弱的时代,如果说一件真正的艺术品的面世具有任何重大意义的话,该书的出版就是一个历史事件……小说写得十分出色,是多年前凯鲁亚克本人为主要代表,并称为“垮掉的”那一代最清晰、最重要的表述。
他和他的朋友们是“叛逆的一伙”,他们“试图用能给世界一些新意的眼光来看世界。试图寻找令人信服的……价值”。他们认为这一切通过文学都可以实现,产生了要创造一种批判现有一切社会习俗的“新幻象”的念头。
《在路上》里的人物实际上是在“寻求,他们寻求的特定目标是精神领域的,虽然他们一有借口就横越全国来回奔波,沿途寻找刺激,他们真正的旅途却在精神层面;如果说他们似乎逾越了大部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他们的出发点也仅仅是希望在另一侧找到信仰”。
《在路上》可以同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和弗·斯科特 ·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并列为美国的经典作品,被现为探索个人自由的主题和拷问“美国梦”承诺的小说。
优质英语培训问答知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