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轻松小绿植
雨夜,电闪雷鸣,阿勒泰地区迎来了近百年来最大的一场降水。 贺琳透过舷窗往外看去,一切都是模糊的,一层浓稠的水幕顺着窗外由右上快速滑向左下,一层接着一层,好像永远不会褪去。她伸出自己不大的手掌触碰着舷窗上的玻璃,寒冷的感觉停留在她的指尖上。稍远的地方,她依稀辨认出两架运输机的夜航灯,那是两架从甘肃酒泉军用机场起飞的运-3运输机,贺琳知道,上边装有那些她见过和没见过的大大的医疗器械和设备。窗外雷声不断,突如其来的闪电撕碎了无边的黑夜,让窗外的水帘变成了银色的流金。贺琳的呼吸逐渐加快,她不经意的握住了舱壁的把手。闪电的强光让她非常恐惧,仿佛回到那个晚上。好在机舱内引擎声轰鸣,隔着厚厚的机舱,外面的雷声被遮盖了起来,变的不那么吓人,这让贺琳感到抓住了一根心安的稻草 机舱内一声短促的警报响起,舱门边的红色的灯也随着亮起,把舱内染成一片暗红色。在充满微弱红光的机舱里,几十名孩子迅速从机舱内靠背座椅上站了起来,无声的排成两排纵队面向机舱大门。他们身穿着了暗绿色的迷彩服,代表医护的红色十字臂章佩戴在每人的右臂上, 在胸前,红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上有一根手杖,️手杖被两条相互缠绕的蛇紧紧缠住。红光像流动的霓虹,在孩子们的眼睛中闪耀。他们有男孩,也有女孩,所有人都还稚气未脱。在过去大人们还在的时候,他们大多还在念初中,还在享受校园生活的苦乐。但现在,他们有的是已经执掌柳叶刀三年的小医生,有的是在临床一线工作两年多的护士。现在阿勒泰西线战事僵持,又连日暴雨,陆地交通干线已经损毁严重。在两天的紧急培训后,这些小医生小护士们,临时改乘“运-3”运输机编队,飞向祖国遥远的西北边陲。 “注意,要开门了!”引擎的轰鸣声中不知谁大喊了一声。 红灯应声熄灭,黄灯亮起。 机舱液压门缓缓开启。一时间,呼啸的冷风夹杂着浓厚的水雾,猛的灌进了机舱内。很多孩子险些被这突如其来的强风吹倒,光是紧紧握住舱壁上的把手就已经很费劲了,根本不能再向前走一步。一时间,雷声仿佛被某个调皮的孩子调高了音量,狠狠的敲进了所有人的耳朵里。 这时机舱广播毫无征兆的响起了,“赶紧。赶紧跳!所有人马上起跳。我们被敌人的雷达锁定了!再不跳就来不及了!”广播中传来了一声嘶吼,贺琳费了好大劲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这绝对是贺琳听过最难听的声音,在此之前她从不相信一个男生会发出这样的声音,这是一种被极度恐惧和紧张反复加工才会出现的几乎非人的声调。但不管怎么样,至少驾驶员并没有抛弃他们,已经告诉他们如何去做了。顿时舱内乱作一团,嘈杂的声音此起彼伏,恐惧传染了每一个人。他们像扔开烧红的金属般争先恐后的松开了机舱壁的把手,拼了命的在颠簸的机舱里向舱门奔跑。离舱门最近的几排孩子里,胆子最大的几名在听完广播时候就闭上眼睛跳了出去,一切都不重要了,他们几乎把这几天来的跳伞培训内容忘了个精光。剩下的则是几名胆小的孩子,他们依旧把把手握的紧紧的,本能的叫喊,但很快被寒冷且缺氧的狂风灌满了整个肺部,强迫般的闭上了失控的嘴唇。后边离舱门最远的孩子则疯了一般的去推前边的孩子,甚至不顾一切要爬过前边孩子的身体。身体瘦弱的孩子企图重新握住松开的舱壁把手不让自己摔倒在已经变的湿滑的机舱里,但却被后边涌来的孩子挤得前后摇摆不定,一双手在墙上胡乱的抓来抓去。不幸的贺琳排在机舱的最里面。瘦小的她用尽自己全身的力气顶着狂风在往前边挪动,只有在这时,她才觉得无论多快的动作都会变的像蜗牛一般慢。 “他妈的前边的赶紧跳,想我们也跟你一起死吗?”后排的孩子们边骂边用力推着前方的孩子,有几名在舱口还不敢跳的孩子被不断向前的人群挤下了飞机。最开始是一个,两个,后来一团一团的人群跟着摔下去。什么起跳姿势,跳伞高度,去见他的鬼吧。有几名孩子精神过度紧张的大喊,在跳下飞机一瞬间就反射般的拉下了降落伞的拉绳,但并没有像电视纪录片里开出一朵朵漂亮的伞花,却像是被雨夜里几双恐怖的大手拧成了麻花,这时他们才绝望的发现自己已经完全失去生的最后一根稻草。回过神来时自己无法自控的歇斯底里的叫喊着,理智的大坝完全被摧毁了,他们的脸上本应被泪水覆盖,但却被冰冷的大雨冲刷的一干二净。狂风裹挟着几个不幸的孩子,把他们扔到了无边黑夜里的一个毫不起眼的角落里去了。 贺琳满眼惊恐的看着这一切。虽然经历过残酷的内战,但这一切依旧在撕扯着她年幼的神经,但她还是迈开步子往舱门趔趄的跑去,这时机舱里除了依旧把着机舱壁的几个孩子之外,已经没有其他人了,这些孩子或许依旧做着心理斗争,或者根本被吓到根本丧失行动能力了,但这都没有区别。 贺琳走到机舱边缘,她回头看了一眼这些吓的瑟瑟发抖的孩子们,顶着狂风和夹杂的暴雨,对这些人喊道“大家都赶快跳吧,不跳就什么都没有了!”随后贺琳竭力想起跳伞的培训步骤,一跃而下。跳下的瞬间,贺琳把自己的身体张开,她回想着培训时的要领,尽力舒展自己的身体,摆出一个腿部略窄的“大”字。一瞬间,雨水疯狂的砸向她四肢的各个位置,空气此时变的十分粘稠,冲击着贺琳的脸。幸好贺琳佩戴的空气面罩和她的脸完美的贴合在了一起,否则在如此的高空自由落体,呼吸都是艰难的。她恐惧的瞬间,竟然感到一丝兴奋。“活着的人请听好,落地后统计人数,你们会看到地面上的标记火焰,记得往那边靠。”贺琳的空气导管耳机里突然响了起来,这是特别医疗小队队长的声音,贺琳的思绪突然被拉了回来,跳伞让她变的有些飘飘然,居然忘记了自己的任务。 突然西北的天空中突然变的火亮,而且贺琳眯起眼睛注意它时,它还在不断的变亮,贺琳看出来,这个火球是冲着他们来的,几秒钟后,贺琳发现这枚火球的速度其实极为迅速,她瞬间想起了初一时数学老师画过的一个x三次方的图像,在经过1后,几乎就笔直的直冲y轴那并不存在的最上端点。这枚导弹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最后仿佛连火球的形状也渐渐被这飞快的速度拉扁了一样,它的后端仿佛生出了一个小尾巴,尾巴越来越长越来越长,最后变成了贺琳在电视️上看到的火箭发射时尾焰的形状,贺琳惊恐的意识到,这是一枚导弹! 一声仿佛来自贺琳内心的巨响爆发了,贺琳一瞬间觉得黑夜的帘子被粗暴的拉开,虚假的阳光在一瞬间填满了整个荒凉的戈壁。她想扭头去看那架运-3,但是她感到后背逐渐变强的热力,甚至变的有些燎人,她不敢再扭头看去。好在一瞬间后,这种感觉重新被雨水的冲击填满。黑夜也随之宣告阳光死去,整个戈壁又重返冰冷的黑夜。 “运-3被击毁了” 贺琳颤抖着,对着喉式麦克风说道。她想起运输机里那几个死死握住着机舱把手的孩子们,心里被揪的紧紧的。而这时,她突然想起了什么,她急忙扭过头四处张望,但只看到黑夜中一朵还未凋谢的充满硝烟和火焰的死亡之花,其余的两架运-3则消失在阿勒泰的雨夜里,不见了踪影。 “另……另外两架运-3呢?”她颤抖的声音通过小队的无线电传到了还活着的孩子们的耳朵里,他们有的已经在雨夜里安全着陆,有的依旧紧张的操控着降落伞的方向不被狂风吹翻,但听到贺琳的声音后,他们不约而同的向那片现在已经空无一物的夜空中看去。 这支编队从兰州机场起飞进入阿勒泰地区时,俄罗斯孩子的预警机雷达就已经察觉到并紧紧咬住了这些运输机,三分钟前,在哈萨克斯坦库尔奇军事基地,5枚带有激光制导的“掷矛手”防空导弹飞向了孩子们的运输机,只有贺琳所乘的运输机驾驶员发现了飞机被锁定,匆忙发布逃生广播随后跳伞,其余两架运输机的驾驶员还只是仅仅停留会开的程度而已。也因为这样,早在跳伞两分钟前,他们被突如其来的导弹分别命中,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被厚厚的机舱壁所遮蔽,贺琳一行人甚至没有察觉到远处闪动的爆炸火光,就这样,年轻稚嫩的驾驶员们过早的离开了这个动荡的时代。 但没有时间悲伤,手腕上的气压表在疯狂的振动,贺琳回过神来,发现指针指向了开伞的最低高度,随着高度的下降,呼啸的狂风变得稍微温和一些,但暴雨依旧,贺琳把手摸向了已经湿透了的伞包把手。 几乎无声的,黑夜里最后一朵伞花悄然开放,虽然风小了很多,但对于贺琳来说,控制降落伞依旧非常吃力,她看向四周,周围没有任何同伴,只有无尽的黑夜和打在脸上的雨水。她突然觉得自己掉进了《喂!出来》里边那个仿佛无限深的巨坑。深不见底的黑暗吞噬她只是迟早的事。 “还有人没有降落吗?”步话机在静谧的黑夜里响起。贺琳的思绪一下子被拉了回来。 “有,我是6队的副队长,贺琳。”贺琳对着步话机大声的喊道。 “贺琳,我们马上在地面上做降落标记,是绿色的冷光棒。请注意靠近。”这是一个沉稳的男孩子的声音,一颗从跳伞逃生时的石头终于落地。她松了一口气,想活动一下手指,这时她才注意到手指已经被降落伞辅助带勒的有些疼痛。 远方一点微弱的绿光,像初升的第一缕阳光,射入了贺琳的早已习惯黑暗的眼睛,然后是第二点,第三点。一大堆绿色的光点终于汇聚起来,照亮贺琳黑色的瞳孔 “是降落标记!”贺琳大喜,她重新根据风向笨拙的调整降落伞的路线。根据刚才降落标记的位置,贺琳推算自己还距离地面已经非常近了,她微微屈膝,以吸收落地时的冲击力。在训练时,整个医疗部队采用的是军队革新过的侧滚翻式着陆法。能有效减少落地时巨大的冲击力对人体的伤害。 终于落地了,贺琳借下落的惯性侧身开始滚动,缓冲了大部分的冲击力,借助闪电的瞬间强光,她看清了自己的着陆地,这是一块充满泥泞的沙地,大大小小的水坑布满了这片沙地。磨盘大小的石块凌乱的分布在四周。而集合的绿光就在前方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闪耀。她解开自己的伞包,站起来后下意识的想和训练时一样拍掉身上的沙土,但一瞬间,她就发现支撑自己起来的双手上沾满了黄色的沙土,她的身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每一件衣服全部都湿透了,原本干净的军服沾满了泥浆和沙土。自己的头发上也全是粗糙的沙粒。贺琳愣了一秒,但她咬了咬牙,朝着远处的绿光笔直的跑去。 一路崎岖不平,就算有强光战术手电的照明,还是会走到很危险的地方去,贺琳险些跌进一个十几米深的沟壑。沟壑里,巨大的洪流裹挟着百年来沉积在此的泥沙碎石,咆哮着向沙漠里不知名的某处奔流而去。 “但愿没有人在降落时掉到这里。”贺琳心里一阵后怕。她向远处看去,绕开这条因暴雨复活的怒河。终于,在翻过最后一个低矮的沙丘后,亮绿色的光的亮度达到了峰值,绿光周围,已经聚集了十几个人,他们在不停的忙碌着什么。贺琳朝他们跑去,有一个比她高一个头的男生率先注意到她,对着另一个方向大喊到:“这里!这边又来了一个!” 不远处几个人打着手电闻声赶来,贺琳打量着这几个人,他们也像是在泥浆池里泡过一样,浑身上下脏兮兮。“姓名?”有一个身材明显比其他人魁梧的男孩子在几个人的簇拥下跑了过来,他们把自己的军服脱了下来,给这个男孩子遮雨,等他跑到贺琳面前时,贺琳看到他的手里拿着一份纸质的文件。尽管如此,那份文件不少地方也受了潮。 “我是6队的副队长,贺琳”贺琳说道。 “贺琳。。。。贺琳。。。。”那人在纸上找了好一会,又翻了一篇之后抬起头问道“是上边一个加下边一个贝吗”贺琳点点头,男孩子看了半天,终于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根笔,在纸上打了一个勾。然后他抬起头看向贺琳“6队是华北第三医院的吧,你去那边找你们队的人,天一亮我们就出发” 贺琳条件反射的看向自己的手表,现在是午夜两点。贺琳点了点头。她没有说什么。男孩子们向不远处指了指,在一块岩石的阴影下,好像有不少人挤在下边。 贺琳在雨中慢慢的走了过去,那是一块巨大的岩石,但底部不知怎的被侵蚀出了一个凹陷,意想不到的可以避雨。满身泥泞的孩子们挤在一起,互相取暖。 贺琳把手电光调暗了一些,向人群照去,但她并没有看见任何人。一阵疲倦突然的袭来,她倒在了一个人的身上。 “轻点!”被撞到的人不耐烦的说了一句,贺琳道歉后,闭上了双眼,逐渐沉入了梦的深渊里。 一切都静悄悄的。阿勒泰的夜,雨依旧下着。不管是醒着的 睡着的孩子,他们在一瞬间之间都长大了 这就是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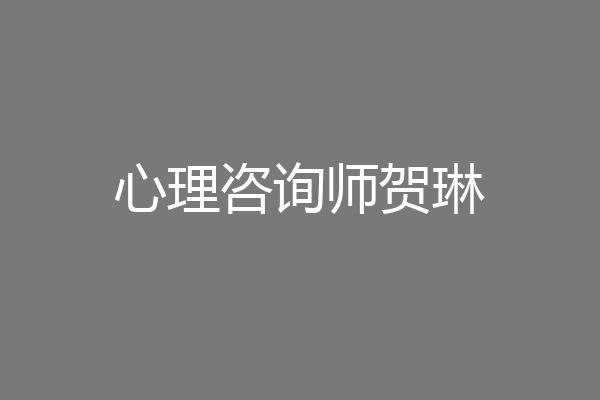

摄氏三十八度
愿无岁月可回头,且以深情共白首。
我是一个很好奇的人。
我也是一个用情很深的人。
对于一个又好奇用情又深的人来说,其实爱一个人并不是一件难事。可是这个世界上最难做到的,仍旧是爱一个一直变化着的人,让“新爱”不断涌出,并且跟他共同创造生命史,完成从“我”到“我们”的转变。
我想知道,为什么我对你不再好奇了
我曾经答应过你的,我要把比较禁忌的话题都好好研究一番,然后邀请你一起探讨。本周是2016年的最后一周,我已经在这一年里跟你探讨了死亡和丧失,所以最近可能还会邀请你探讨一下性。为了研究性,我让好朋友给我推荐了一部韩国情色片,叫做[爱人](看情色片的理由说得好冠冕堂皇,哈哈)。
这部电影的开始,女主就被在电梯里结实的一位男性吸引了,后来两个人就发生了性关系。而女主其实马上就要跟与自己相恋7年的未婚夫结婚了,这段突如其来的“艳遇”,也让她感到不知所措。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她跟未婚夫的一段对话:
女主:“欧巴,我们晚一点结婚吧,明年再结可以吗?”
未婚夫:“为什么要晚一点?我们都已经在一起7年了,你知道的,虽然我们是彼此的地狱,但是我们谁都离不开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狱,我们就结婚吧!”
女主:“可是我凭什么要成为你的地狱?”
在上周五的文章我们,到底是彼此的天使还是魔鬼?|我眼中那个“可能”的你里,我邀请你一起探讨了我们到底要成为彼此的天使还是魔鬼这个话题,今天的文章也可能是那个话题的一个延展。
女主的这句质问,一直回响在我的脑海里:可是我凭什么要成为你的地狱?
我们跟一个人从相识到相爱,到彼此亲密无间,再到了如指掌,是否就会变成彼此的地狱呢?地狱是爱情的必然走势吗?我想显然不是,但是我们如何能避免成为彼此的地狱,避免对彼此的不再好奇,不再欣赏,不再感受到自由呢?
这件事情可能要从我们不再对这个人好奇开始。
当然如果我们再追根溯源一些的话,这件事情,可能还跟我们早就放弃了对自己的好奇有关。借用一句很流行的话说:有的人在20多岁的时候就死了,只是到了80多岁才埋葬自己。
最近我的一些相亲经历,也让我看到一些男孩,他们跟我一样,都只有30岁,却把每天都过得没有任何差别。他们会告诉我:“我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可是我还能怎么样呢,所以就这样吧!”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我已经对自己的在世热情不好奇了,我不好奇如果去追求我热爱的东西会有怎样的不同,不好奇还有没有对我来说更有意义的事情,不好奇我的全部天赋和才华可以怎样make a little difference,不好奇如果我每天全情投入地享受工作的那8个小时,生活会有什么变化,这些,虽然我只有30岁,但是我都不再好奇了。我就等着养老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对于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说,这份对自己的好奇,正在一点点“死掉”。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的生命有“无限可能”,我们渴望看到自己“长大之后的样子”。可是等我们真的长大了,反而发现自己生命的轨迹,好像越来越狭隘;前方的路,好像都看得到尽头。
对自己好奇,是我们相信,今天的我,真的和昨天不一样,而明天的我,又会和今天不一样;在不同的情境下做着同样一件事情的我,并不一样;跟同样的人一起做同样的事情的我,每次也不一样。我好奇自己的一切,我今天小小的不一样:我对自己想要什么,喜欢什么,什么对我来说最有意义和价值,所有这些事情的想法和感受,因为今天经历的事情,有了怎样的变化?什么让我觉得快乐,什么又让我难过?如果重新让我过一遍今天,我又做什么不一样的事情?今天我最欣赏自己哪里?今天我给这个世界一点什么不同?这个好奇,可以是无穷无尽的。
一个对自己没有好奇的人,最后也会对所有的关系失去好奇,不管开始的时候,这段关系带来了怎样的“新鲜”。
因为不用任何努力便能感受的“新鲜”,是十分有限的。就像我第一次跟你介绍说我的职业是心理咨询师时,你可能会觉得惊讶:“是吗,哇塞,我还从来没见过活的咨询师呢!”可是当我第二次跟你说到自己的职业时,你可能就需要一些好奇心,才能感觉到新鲜,因为你已经知道我是咨询师了。
当所有容易看到的“新鲜”都被看到后,当我们从彼此陌生,相互探索的阶段,到了后面彼此熟悉的阶段,是否还能带着好奇去探索对方呢?
也许你要反驳我说:可是我的确就是很了解伴侣了呀,她/他还有什么可了解的!
可你知道吗?这就是生而为人最奇妙的地方:如果你愿意坐下来,安住于当下,好奇地,全身心地听一听对方想说什么,你就会发现,就算是再无聊的生活,你也总能用自己的好奇问出一些从前你不知道的东西,因为探索一个人,本就是无穷无尽的。
这种不可穷尽就在于首先我们是非常复杂的,复杂到很多时候我们都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做出某个选择或者突然间有某种感受。其次,我们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包括我们跟彼此的关系。这个变化的过程多数情况下是缓慢的,有的时候是戏剧性的。
所以并不存在我们把一个人“探索完了”,这个人也包括我们自己。
但今天除了好奇,我还想邀请你走得更深入一些:除了好奇和欣赏,我们要怎样在对话中,让彼此在爱情里更加自由,而不是成为囚禁彼此的地狱?
我想给你一双翅膀,让你逆光,也能飞翔
我想每个人都是向往自由的。那么亲密关系是否是自由的“枷锁”呢?
如果不是,我们又要如何给予彼此足够的空间,让对方在我们的爱中,也能拥有最自由的空气?
在这里我想再讲一个小小的故事。
电影[革命之路],被很多人戏称为[泰坦尼克号]的续集。因为莱昂纳多和凯特在时隔11年之后又聚到了一起,这次他们过起了夫妻生活。
当他们第一次见面,他是高谈阔论的有志青年,她是向往成为名演员的未来之星。而如今,婚后的他们变了。他变成了在公司做不喜欢工作的无聊上班族,她成了不入流的糟糕演员。在一次演出后,丈夫Frank与妻子April大动肝火,两人多年的积怨终于爆发。
悲痛的April整理照片,发现Frank年轻的照片,想起他曾经描述的“美好的巴黎”,她提出了一个计划“全家搬到巴黎”,以拯救这个家庭。但是,这看似遥不可及的计划,却成为了催化剂,将两人推向婚姻更痛苦的深渊。
Frank并不愿意搬去巴黎,而对生活无比失望的April却意外发现自己怀孕了。April不愿意要孩子,而堕胎在当地又是违法的。电影的最后,April因为自行堕胎而不幸身亡,Frank也在绝望中搬离了他们住的,那条叫做革命之路的巷子。
April曾对Frank说:“你只是让我陷入生活的圈套,让我感受你所让我感受的。”
这个故事不禁让人唏嘘:这对被住在革命之路的其他邻居视为金童玉女的夫妻,怎么就婚姻成了彼此的囹圄,甚至是真实的坟墓呢?
电影的悲剧固然发人深省,但导演并没有给到我们,如何在对话中,给予彼此最大自由和尊重的出口。我想在这里用有限的文字,尝试着邀请你一起去做这样一个探索,然后看看我们会走到哪里。
1.我不用任何“历史”来定义你的现在和未来(I don’t define your present and future with your history)
心理学里有个词,叫做身份认同,或者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标签。
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份认同并不完全由我们来决定,这就好像是一个蝴蝶效应:开始的时候,这个别人对我们的身份认同来自于我们与别人互动的结果,我们在其中也建构着自己的身份,但渐渐地,这种身份认同就像自己有了生命,开始反过来定义我们是谁。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写作是一个我的“在世热情”,开始的时候,我的确是在写作中被一些朋友认识,大家也会给我很多关于写作的反馈。但渐渐地,“作家”这个身份开始有了它自己的生命:不管是熟悉的还是素未谋面的朋友,在我没有写作的那段时间里,会经常来询问我:“Joy,怎么你最近没有写东西呢?”或者如果他们认定了我的写作是某个风格,如果有一天我写的东西跟平时的风格不太一样,他们也会来告诉我说:“Joy,我不喜欢你现在的风格,能不能多写写你原来那样风格的文章?”
也就是说,我们创造了我们自己的身份认同,而这个在社会中的身份认同,会反过来定义我们。
一个从前是“小偷”的孩子可能决定不再偷东西了,但是其他人对他的身份认同已经形成。于是,别人在丢东西的时候,还是会在第一时间怀疑是他偷的。这个决心不再偷东西的孩子,很可能因为别人对于他“小偷”角色的认定,而重新开始偷东西,这就是我说的,身份认同,会反过来定义我们是谁。
我想如果在爱情里,我们要给彼此最大的自由,就要学会不用任何“历史”去定义的现在和未来,不给对方来自我们“标签”的枷锁。
在这里,我又想起了李安的最新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
林恩在战场上解救战友的过程,无意中被战地里的摄像头拍到,休假回国期间,他顿时成了全民英雄,虽然很明显地,他很有可能得了创伤后综合症(PTSD)。林恩也很害怕回到那片可怕的战场,并且他姐姐因为担心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一直希望这次休假之后他就不要再回去了。
可是最终他还是回去了,临走前的一个细节意味深长:
林恩在休假期间认识的一个美女啦啦队员,在他临走时,含情脉脉地来看他。他激动地对她说:“我差一点就不想回去了,想跟你逃走。”
美女望着他,脸上并没有不舍或者幸福,而是疑惑地说:“逃走?可是你不是全民英雄吗?”
林恩那个时候到底有多失望,我无从知道,但他只是默默地说:“是啊。”然后默默回到了送他回战场的车上。也许在那一刻冰冷的现实让他意识到,原来爱情只是一个幻影,美女爱的,是他“全民英雄”的身份,而不是他。
我想最自由最有力量的爱,首先是尊重彼此,让彼此自己定义此刻和未来的她/他是谁,而不是用我们的判断来定义他们。并且在此基础上,帮助他们建构他们自己喜欢的身份认同。
举个例子:假设我的男朋友从前约会时迟到过几次,但其实他自己也非常不喜欢迟到,不希望自己是一个经常迟到的人。那么我要做的,可能不是评判他的迟到,说他“就是一个爱迟到的人”,并且问问他,我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他更守时。并且在他守时的时候,欣赏他,好奇地询问,他是怎么做到守时的。
1984年,30岁的李安结束了在纽约大学电影制作研究所的学业,开始了为期6年的“在家闲置”生活。他阅读、看片、写剧本,包揽了所有家务,但是他一心想建构的身份,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导演身份。当时,家庭开支则完全靠仍在攻读伊利诺大学生物学博士的妻子林惠嘉支持。林惠嘉并没有用“家庭煮夫”的身份定义李安,而是帮助李安建构他喜欢的导演身份。6年后,36岁的李安完成了[推手]的剧本,并且拿到了40万元奖金,这笔钱,让他从此有了独立执导影片的机会。
不让我们过往的“标签”定义我们的现在和未来,也不用过往去定义我们的伴侣,放下“我们希望他们成为什么人”的期待,然后帮助彼此成为我们各自喜欢的样子,也许就是爱情就美好的模样吧!
2.避免任何形式的独白(avoiding monologue of any kind)
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对话进入一种“僵局”或者“死胡同”里的时候。你们总是因为同一个问题不停争吵,却从来没有过任何结果。
当我们的对话进入到了一种“僵局”时,那几乎就可以说明一件事情:我们根本不是在对话,而是在各自的世界里独白。
那么到底什么是独白呢?哪些对话看似是在交流,而实际上却是在独白呢?在这里,我想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观察,列出下面几种可能性,但实际的情况可能并不限于这些可能:
试图让对方同意自己的观点,争辩,或者试图说服对方。
把对方曾经暴露的脆弱当成是攻击她/他的武器。
用对方的过往来定义和解读她/他此刻的行为,而不是真正对对方此刻行动背后的动机好奇。
滔滔不绝地宣泄自己的情绪,不给对方回应的机会。
在对话中陷入到对问题的关注里,看不到对方的努力,不容易和值得欣赏的地方。
带着预判,预设,和对方“应该”怎样的评判,没有好奇。
在对话结束之后,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并没有任何变化。
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最后一点:当你结束一段对话时,如果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并没有因为对话而发生任何改变,那么你很可能就是在独白。因为对话的本质,就是情感和思想的交流,如果这种流动发生了,你们一定会彼此影响,并且共同创造出一些从前没有的东西。
欧文亚隆曾经小说里,这样嘲笑一名“资深”的咨询师说:他骄傲地宣称自己在一个10年的小组里,是唯一一个没有任何变化的人。可是我为他感到悲哀。一个人怎么可以在10年的小组里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呢?真正有效的交流,一定是相互改变的。
我们要如何做到避免独白呢?
在我整个心理学和咨询学习的历程里,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反思和觉察了。
我们开始好奇地问自己:咦,刚刚的对话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怎样一个过程?我在这个过程中的想法和感受有变化吗?如果没有变化,那么刚刚我“独白”的动机和目的到底是什么?我是怎样陷入到这种独白中的?如果我想要避免这种不断重复的独白,可以做些什么不同的事情?我对对方有好奇吗?我刚刚是否带着自己的预设和评判,而不是试图理解对方真正想表达的意思?
当我们开始停下来反思和觉察时,就是我们独白停止的开始。
而学会放下所有的预设,评判,担心,焦虑,恐惧和“应该”,或者即使我们无法放下,至少我们可以觉察到它们,并且跟对方公开化自己内心的这些预设,评判,担心,焦虑,恐惧和“应该”,都是一份对话的邀请。
我一直相信,爱是一个相互影响,共同创造的过程。我们所说的“不断创造新爱”,就是在这个共创的过程中产生的。而爱的消亡,也从我们的“独白”开始:我们不再对彼此好奇,不再能放下自己的预设,评判和偏见去全心聆听,不再欣赏和好奇我们跟彼此的不同,不再关注对方在过程里所做的努力,不再想要暴露自己真实的脆弱。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把自己囚禁在了自己的宇宙中,没有流动,就不可能有“新爱”产生。
3.不断扩大对话空间(enlarging dialogical space)
另一个给予彼此自由的对话方式,就是不断地扩大对话空间。
那么啥叫对话空间呢?打个比方,刚刚我们已经说了避免独白的重要性,反过来说,就是让对话流动起来的重要性。这个流动,就像一条河流。河流的流动是需要空间的,同样,对话要不断流动下去,也需要更大的空间。
这个空间通常是依靠我们全心投入,用情专注的聆听,陪伴,好奇,以及欣赏造就的。在上一篇文章里,我已经跟亲爱的你,逐一讨论了这一点,并且同时探讨了扩大对话空间这个话题。
但是今天我想继续邀请你探讨:我们要如何在亲密关系中,给予彼此更大的对话空间,尤其在对话进行的很艰难的时候。
后现在合作对话创始人贺琳.安德森(Harlene Anderson)曾经提出,如果要扩大对话空间,我们就不仅仅要关注对话的内容本身,还要关注对话过程。
当我们能够跳脱出对话的内容(“你为什么就不能早点回家?”或者“你为什么就不能每周给我多做爱几次?”),看到整个对话过程:看到我们是带着怎样的意图开始跟对方的对话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是独白,还是我们容许自己去聆听和理解对方,我们的想法和感受在这个过程里是否有变化,我们是否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我们的对话结果是否令彼此满意,等等,当我们能看到整个过程,我们就不会再深陷在“问题”里无法自拔。
昨天中科院心理所的一位朋友采访我,讨论我在咨询中的成功和失败案例,我突然在这个过程里清醒地意识到:从前所有我觉得很艰难的对话,都是因为来访者深陷在“问题”或者内容里,而我并没有帮助她/他很好的打开对话空间。
我想举个例子。比如可能一位来访者在咨询过程中不停跟我抱怨他的老婆如何不好,并且深陷这种委屈,愤怒,悲伤和怨恨中。如果我发现我的提问并没有让他开始反思和觉察自己,那么可能我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打断他的独白,然后询问他:“刚刚你表述的这个过程里,你的想法和感受有什么变化吗?你为什么想要讲这段话呢?”
甚至如果我发现我们的对话没有任何进展,我会坦白地跟对方说:“我发现刚刚我们的对话有些艰难,你是怎么看待这个过程的呢?这些话是你最想让我听到的吗?你还希望我听到什么,我再多听到些什么,可能对你更有帮助呢?有什么是你想告诉我,但是憋在心里没有跟我说的吗?”
我想在爱情中,我们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如何让彼此在艰难的对话中,可以打开更大的对话空间,让对话能够持续进行?
我想尝试着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些回应:
不仅仅关注对话的内容本身,同时关注整个对话过程和变化。内容和过程,同样重要。
反思和觉察每个艰难的对话过程,觉察自己是否在独白。
让对话慢下来,给反思和内在对话流出空间。慢既是快。
在觉察到自己已经陷入到内容和所谓的“问题”中时,能够再次回到过程上,对过程好奇。
尝试着转换角度,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件事情。
关于最后的“转换”角度这一点,我还想再做一些说明。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彼此理解,是因为我们都太坚定地站在了自己的解读和立场上,无法从对方的意义地图出发去诠释同一件事情。
那么这个时候,从更多元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就会为我们创造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可能性。
讲一个我生活中的故事。
之前好朋友跟我讲他一直想辞职,却无法跟父亲开口,害怕父亲的评判,也害怕他的不理解。于是有一天我邀请他跟我做一个“角色扮演”:我扮演他,他扮演他父亲。
在十几分钟的对话之后,他竟然奇迹般地,在父亲的角色中,同意我这个“儿子”辞职了。后来他跟我说,在这个过程中,他有两点体会:一个是他从我身上学习到了如何跟父亲有不一样的交流方式和表达,另一个是也许他的父亲没有他想象的那么不通情达理。
这就是转换视角的力量。同样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可以跟伴侣交换视角,会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是我们的一个共同的好朋友看到这件事情,她/他又会怎么说呢?如果是一个我很敬佩的人,比如贺琳.安德森,她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
不同的视角,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这是空间打开的一个特别有效的方式,也是为什么,有些时候第三方反而看得更清楚的原因。就是我们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4.从“我”到“我们”:营造一种具有“生成性”的对话过程(facilitating a generative dialogical process)
刚刚我们说到,任何真正的对话,都是一个相互影响,共同创造的过程。我们管这样的对话,叫做生成性对话。
在爱情里,我们总会从“我”变成“我们”。这个“我们”,就是彼此共创出来的生命史。生命中大大小小的决定,我们彼此的梦想和担忧,希望与恐惧,期待与失望,快乐和悲伤,都需要彼此的见证和陪伴,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共同创造出从前没有的美好。
贺琳.安德森曾经说过一句平凡而动人的话,她说:对话是每个当下自然,自动发生的活动。她又提出了以下几个有趣的特征:
你可以准备对话,但是不能提前计划或者设定结构。
对话不能设定步骤,对话过程不是线性或者可重复的。
对话不能被实施,被操控和管理。
对话像根茎,网络状。没有所谓的正确的入口或者出口。
对话是随机发生的,它漫游,带来惊喜,会在不可预期处转向。
对话不必是连续的,但必须是持续的(可以不断发生)。
前3条跟我们曾经提到的不预设和不评判有关。现在我想说说后三条。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语言就像一个迷宫,哪里都是出口。所以贺琳也会提到“对话像根茎,网络状。没有所谓的正确的入口或者出口。”意识到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既然语言并没有正确的入口和出口,那么我们就不用计较所谓对话的“结果”如何,也不用计较我们开始对话的方式是否足够“正确”。可能你要问了:如果不计较结果,那我对话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就像我刚刚说到的,对话是一个相互影响,彼此改变,彼此共创的过程。所以只要你们的想法在这个过程中有所改变,对话就已经在流动了。这个流动是在我们对话结束之后仍旧在持续着的一种力量,也是为什么很多来访者在这次咨询结束,下次咨询还没有开始的一个星期里,能够持续有很多反思和觉察的原因:因为我们的对话虽然结束了,但是它却打破了我们原来内心的独白,我们的内在对话也开始流动起来了,有了新的变化。
所以对话的目的是让变化发生,在相互影响中,打破从前的内心独白。
这个过程可能会带我们到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里,自由地做“时空遨游”:回到过去,安住于当下,或者探讨未来。你甚至会神奇的发现,我们还可以一起重新改写过去,共创此刻和未来。
我想到从前自己跟闺蜜的一次对话,发现自己在过往的岁月中,虽然没有正式地谈过恋爱(曾经我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却仍旧在爱情中做了很多宝贵的探索。在这些探索中,我一次次发现自己的勇敢,善良,一次次看到自己的成长和不同。我们一起改写了我一直觉得自己“感情空白”的标签,看到我是如何在这些对爱情的探索中,不断地成熟睿智起来,温暖而坚定地修炼着爱的艺术,而且不止是在爱一个人,而是爱整个世界。
愿无岁月可回头,且以深情共白首
在结婚的时候,我们对彼此的誓言,也许是同甘苦,共患难的白首不离。
可是这份白首出了缘分的成全,和我们开始拥有的深情之外,也需要我们历练出足够的智慧。
我们,如何在一份“旧”的关系中,不断创造出“新爱”?
我们,如何在婚姻中给予彼此飞翔的翅膀,而不是精神的囚牢?
这份智慧,需要在每天的生活中修炼。
上面的讨论仅仅是一份邀请你探索的开始,它是我探索到现在为止,可以叫出的一份答卷,而我相信,它也将随着我不断探索,不断演化出新的想法。那么你的答卷是什么呢,你持续的探索,又给了你怎样在对话中,去创造“新爱”的启示呢?
爱的最终意义是融于生活,而不是占据生活。
愿我们,都能在对话中,学会爱的艺术!
优质心理咨询师问答知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