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虎呆呆漫步
给你个论文做例子,希望对你有帮助。不学诗无以言———《诗经》在春秋外交中的作用 “不学诗,无以言”出自《论语》,是孔子对《诗经》实用价值的概括。孔子设教,尤其重视《诗经》的学习和运用。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专对”,指外交场合独立谈判酬酢,赋诗言志以应对诸侯的意思。因此,这里的“言”不是一般意义的讲话,主要指外交语言(外交辞令),有场合的限制。“不学诗,无以言”是说不懂《诗经》,不会赋诗、用诗,就没法参加外交活动。而赋诗以言志,可以说是孔子教育的重要内容或培养目标之一,在外交活动中,也是春秋时期特有的外交现象。“不学诗,无以言”正是对春秋近四百年赋诗言志活动的总结。春秋时期,大夫们出使别国,根据礼仪,赋诗成为外交中不可缺少的一个过程,《左传》多有记载。那时一个大夫不会赋诗就意味教养的缺乏,没有“出使专对”的资格。在周代,因赋诗不当引起国家纷争的事偶有发生。《左传·昭公十二年》云: “宋华定来聘�6�8�6�8公享之,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昭之曰:‘必亡。宴语之不怀,宠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将何以在?’”这是对华定不知赋诗的批评。可以想像,赋诗不但是一项基本的外交技能,而且可以从使者的表现看出一个国家的前途。正如班固《汉书·艺文志》所云:“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必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春秋末期的孔子,掌握着西周典籍,又耳闻目睹了赋诗言志的事实,颇有感触地讲“不学诗,无以言”,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现实的指导。以诗的语言作为外交辞令,实在是文化史上奇特的现象,它全整地反映了《诗经》作为一部典籍如何作用于一代社会,如何影响华夏族的语言表现力,并进而塑造了中华民族温柔敦厚的性格,是很有意义的。惜乎学界尚未充分重视,偶有论述,也多对“赋诗言志”作概念、内涵性的解说(如顾颉刚著《古史辨〈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本文尝试从《诗经》在春秋外交中的作用入手,管窥其在文化史上的意义。《诗经》在春秋外交中的作用,概括地说,就是有效地参与外交活动,树立了含蓄外交的风范。一、诗言志能够有效地参与、推动外交活动,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内容是决定性的因素,赋诗之能言志,首先在于《诗经》所含的人文精神和内容之广阔适合多种外交场合需要。如《左传·襄公八年》盟主晋范宣子访问鲁国,商量用兵于郑的共同行动,全部外交过程以赋诗完成:“公享之,宣子赋《扌票有梅》,季武子曰:谁敢哉?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欢以承命,何时之有?”武子赋《角弓》。宾将出,武子赋《彤弓》。宣子赋《扌票有梅》,以女子希望及时婚姻作喻寄意鲁及时出兵;因晋为盟主,相较鲁如“草木”之“臭味”,只好同意,于是赋《角弓》,以“兄弟婚姻,无胥远矣”作答;宴会最后,武子又赋《彤弓》(本为天子赐有功诸侯之诗)表达对晋悼公继承文公霸业的赞美、预言和祝福。从提出要求到答复要求以至宴会告结,整个谈判过程简洁而又明了。“春秋无义战”。襄公二十六年晋平公为强齐伐卫,公然干涉卫国内政,卫侯稍有过问,便“执而囚之”。面对这样一个主观、刚愎、暴戾的晋君,其外交争端如何解决?且看齐、郑二君的表现:秋七月,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兼享之。晋侯赋《嘉乐》,国景子相齐侯,赋《蓼萧》,子展相郑伯,赋《缁衣》。�6�8�6�8晋侯言卫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国景子赋《辔之柔矣》,子展赋《将仲子》,晋侯乃许归卫侯。这次发生在盟国(齐、郑)和盟主(晋)之间的赋诗活动,其核心是讨论对卫侯的处置问题,齐侯、郑伯意图说服晋公,而任务落在国景子和子展身上。如果说晋公赋《大雅·嘉乐》“嘉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是向齐郑二君致欢迎词,那么国景子赋《小雅·蓼萧》“我心写(“泻”,舒畅)兮”、“燕笑语兮”是渲染宾朋相聚时和睦亲密的气氛,“为龙(宠)为光”、“宜兄宜弟”赞颂晋公又自占了身份,这种赋诗是寒喧、客套,然而这种以诗为形式的客套实在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以及子展《郑风·缁衣》“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粲兮”,都以亲密的家人口吻把国际关系人伦化亲情化了,实际是盟国向霸主示意友好,疏通了关系,稳定了外交心理,使谈判在和睦的气氛中进行。接着有了交锋,“晋侯言卫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于是国景子赋《辔之柔矣》:“马之刚矣,辔之柔矣。马亦不刚,辔亦不柔。志气镳镳,取予不疑。”这首诗以“赋”的手法铺陈马与辔的关系:柔能克刚;马刚,辔则柔,马不刚,辔亦不柔;所以即使“志气镳镳”,也“取予不疑”。其中以宽政安诸侯的道理在以柔驭刚的譬喻中已经不言而喻。令人惊叹的是,这种道理竟用诗的语言唱出来,在“刚”与“柔”的对举中,在“不刚”与“不柔”的逻辑中,在“志气镳镳”的形象中,尤其是“之、矣”辞气回旋,极尽感情变化之能事,形成起伏波澜,带来丰厚的意蕴,比单纯的散体语言更加流转疏放,使得内容与情感、语言与声韵一箭双雕,晋公焉能不动情又晓理?如果说作诗者的动机是感性的(《诗经》作品大部分是民歌),那么赋诗者则完全是理性的,经过了理性的揣测、判断、选择的过程,而赋诗的效果(或者说在听诗者),既诉诸感情又诉诸理智,既有深刻的感染力,又有理性的说服力,这就是赋诗言志独特的效果。回到上例,我们看子展赋诗《将仲子》这一特点更明显。子展借一弱女子的口吻暗示对晋国的态度,赋诗重点在第三章后半:“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原诗直抒胸臆,语气随心理的微妙变化而一波三折,但在特殊的外交场合,字面的意义就突现出来:“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可以看做是一个设问,提供“爱”与“人言之畏”两种选择;然后在“仲可怀也”的坦白中,“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的吁叹中,情感的重心逐渐地倾向了后者。而子展借此诗表明对晋对卫侯的态度,颇似“两点论、重点论”的逻辑:虽然一向尊重您,但在这件事上,您要考虑舆论的影响啊。对晋公的劝说明确而又巧妙极了,而听似无奈的语气也透露未失去作为盟国的“谦卑”。两首赋诗,终于使“晋侯乃许归卫侯”,而《诗经》在外交上的说服力也由此可见了。以上摘自:《太原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2年1期 91-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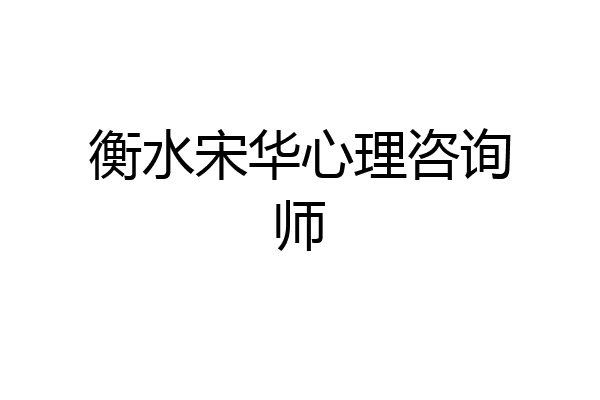

兔宝宝装饰
这要看你的兴趣了,你想学什么,你就必须注入百分百的精力。但是那些你不喜欢的,你也要看看,当今社会只了解自己喜欢的不行,你必须各科都要有涉猎。这样才能更好地在社会生存下去。加油
优质心理咨询师问答知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