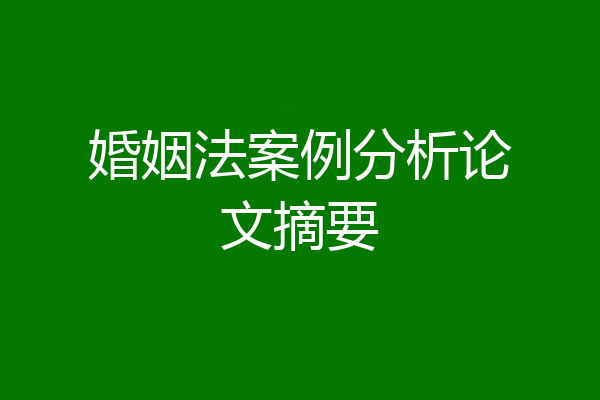569472273
569472273
达永菊诉申朝俭拆毁其离婚时分得的房屋要求赔偿纠纷案 [案情] 原告:达永菊。 被告:申朝俭。 1974年元月,达永菊与被告申朝俭之子申贵德结婚。婚后与公、婆共同生活5年,于1979年随夫申贵德到西宁申贵德单位共同生活。1988年9月,达永菊、申贵德、申朝俭商议,在原籍互助县红崖子沟乡小寨村办一个小卖部,由达永菊经营,以解决达永菊和女儿的生活。此后,由申朝俭以达永菊名义办理了土地使用证、营业执照、银行贷款5999元。达永菊夫妇利用5999元贷款建房4间,购置了货物。建房中用了申朝俭家的杨树3棵,旧窗户两副。房建好后,达永菊开小卖部进行经营。1991年11月1日,申朝俭因向达永菊索要小卖部土地使用证,双方发生纠纷,申朝俭手持木棍和他人将小卖部中的部分商品、柜台玻璃、醋缸等砸毁。同年11月24日,达永菊因与申贵德不和,双方在互助县红崖子沟乡人民政府自愿办理了离婚登记,领取了离婚证书。离婚证上载明小卖部4间房归达永菊所有。离婚后,申朝俭得悉达永菊欲将小卖部卖给他人,即以小卖部是大家庭共有财产,自己是共有人之一为名,于同年11月28日将小卖部4间房的屋顶掀去,并将门一副、窗户三副、大梁两根、檩条16根,椽子46根、货架柜台各3组、玻璃砖13块拉回自己家中。 对此,达永菊以申朝俭侵犯其合法财产权益为理由,诉至互助县人民法院,要求申朝俭归还拉走的财产,修复4间房屋,并赔偿被砸损的财产损失。 申朝俭辩称,小卖部是我们共同商议办起的,土地审批、办理营业执照和向银行贷款,都是我办理的,小卖部4间房屋属家庭共同财产,不是达永菊个人财产。 [审判] 互助县人民法院因申朝俭退休前系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故将案件移送给海东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海东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双方争议的小卖部房屋4间,在互助县红崖子沟乡人民政府颁发的达永菊与申贵德的离婚证书上,明确载明归达永菊所有。申朝俭将该4间房屋顶及门窗折除,其行为侵犯了达永菊的合法权益,应负赔偿责任。达永菊请求申朝俭赔偿砸损的货物,以及申朝俭追要部分贷款的要求,因当时达永菊尚未离婚,与申朝俭未分家另过,属家庭成员之间的财产关系,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四)、(七)项之规定,海东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1992年19月4日判决:申朝俭将拆去的达永菊所有的4间房的屋顶材料、门窗全部返还给达永菊,并赔偿维修费599元,判决生效后一次付清。 对此判决,达永菊、申朝俭均不服,上诉于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 达永菊上诉称,一审判赔偿599元维修费不足以弥补损失。申朝俭抢去的货架、柜台、玻璃未判,申朝俭砸毁的商品价值1499余元未予赔偿,这些是我和申贵德的财产,不属于家庭共同财产。 申朝俭上诉称,小卖部属家庭共同财产,达永菊与申贵德离婚时,登记归达永菊所有,未经他同意,不应判归达永菊。拆去的木材属于自己应有的部分,是本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采取的紧急措施。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达永菊、申贵德结婚后,虽与申朝俭夫妇共同生活,但到1979年,达永菊随申贵德生活,即在经济上与申朝俭互相没有来往。小卖部创办过程中,申朝俭虽然帮助办理了土地使用证、营业执照及贷款,但并未投入资金。杨树3棵和旧窗户两副系对儿子、儿媳的赠予。小卖部房屋属达永菊、申贵德的共同财产。申朝俭伙同他人肆意砸毁商品等,是严重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在达永菊与申贵德离婚后,婚姻登记机关已明确将小卖部归达永菊个人所有,申朝俭仍揭房顶,拆门窗,严重侵犯了达永菊的合法财产权利,申朝俭应负一切赔偿责任。申朝俭上诉理由不足,不予采纳。原审判决只赔偿维修费599元,不足以弥补达永菊的损失,达永菊的上诉理由充足,应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七十五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92年12月26日判决:一、撤销一审判决;二、申朝俭返还给达永菊大梁2根、檩条16根、椽子44根、门1副、窗户3副、柜台3组,玻璃砖13块;三、申朝俭赔偿砸毁达永菊小卖部商品损失799元,房屋重修费用损失1399元,共计299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两个月内交付完毕。 [评析] 本案申朝俭认为双方争议的小卖部4间房屋属于家庭共同财产,在得知达永菊欲将小卖部出卖后,以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为理由,前去拆除房屋顶,拿走木料、门、窗,并认为是采取紧急措施。这种理由是否成立,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第一,小卖部4间房屋是否家庭共有财产。申朝俭认为小卖部的创办,是他帮助办理的土地使用证、营业执照和银行贷款,因而建成的4间房屋属家庭共有财产。但从事实上看,小卖部的创办,目的是帮助达永菊和女儿解决生活问题,又是在达永菊夫妇与申朝俭夫妇分开生活以后;各种手续虽是申朝俭帮助办理的,但是以达永菊名义办理的,申朝俭并未投入资金;小卖部也是达永菊经营的。因此,申朝俭对小卖部的创办和经营,仅是一种帮助行为,并且是当时的家庭关系上的一种帮助行为,并不因此而产生权利请求。所以,该小卖部4间房屋,应属达永菊、申贵德夫妻共有财产,而不属于达永菊夫妇与申朝俭夫妇共有之家庭财产。又,建这4间房时,曾用了申朝俭家中杨树3根,旧窗户两副,建好的4间房是否因此就算是家庭共有财产呢?应该看到,父母(公婆)对儿子、儿媳建小家庭另过,给予一定的财物,在性质上是无偿赠予。双方除有明确约定外,不能因一方接受有另一方的财物,另一方就对所形成的财产享有权利。 第二,小卖部4间房屋属达永菊、申贵德夫妻共有,双方离婚时经过协商,该4间房屋归达永菊所有,并记载在权利机关发给的离婚证上,这是房屋所有权转移的一种法定形式。申朝俭如果对4间房屋属达永菊、申贵德夫妻共有有不同意见,应向达永菊、申贵德主张权利,并通过法定程序解决。在所有权归属问题没有解决之前,申朝俭无权自行采取所谓“紧急措施”,损坏争议标的物。即使该争议房屋是家庭共有财产,申朝俭也无权采取所谓“紧急措施”来损坏房屋,因为这种行为是对其他共有人共有财产完整权的侵犯。 基于上述两点,本案一、二审法院认定申朝俭的行为侵犯了达永菊的合法财产权利,并应承担赔偿责任,是合适的。 但是,由于达永菊的诉讼请求中不仅包括4间房屋损害的赔偿请求,还包括有其与申贵德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小卖部商品被申朝俭砸毁的赔偿请求;申朝俭关于小卖部4间房属家庭共同财产的主张(反诉)也涉及到申贵德的利益。故申贵德在本案中是有部分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法院应告知其诉讼的发生,并由其决定是否参加诉讼。这样,才能理顺关系,准确定性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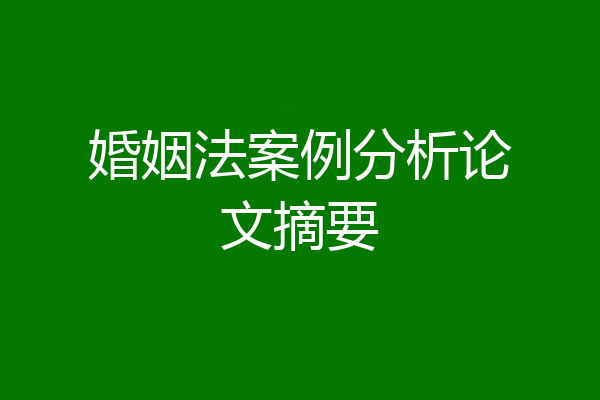
一婚姻法案例分析:沈X为了分得单位最后一套福利分房,经人介绍,找到未婚姑娘张X,并如实告知自己的想法,并承诺房子到手后就与其离婚,并给2万元作为补偿,而且不干涉其生活。登记以后,单位新房分到手,沈X与张X去离婚,到门口张X变卦,多要3000,沈X不给,发生争执。当地婚姻登记机关了解情况以后,撤销二人的结婚登记,收回结婚证。问题:1:本案例的主要法律问题是什么?2:你对本案的处理意见是什么?3:请就本案谈谈你的感受(不少于500字)二婚姻法论文列举一个有关离异后子女探望权问题的婚姻法案例(内容不少于500字,注明出处),并以其中的主要法律问题为题写一篇小论文,题目自拟,总体要求:1.观点明确,立意新颖;2.内容充实,层次清晰;3.文面整洁,不得少于1500字!格式要求案例:题目:文章摘要:(不少于100字)主要观点概括(不少于300字)文章正文:(不少于1500)婚姻法论文(2)列举一个有关家庭成员抚养问题的婚姻法案例(内容不少于500字,注明出处),并以其中的主要法律问题为题写一篇小论文,题目自拟,总体要求:1.观点明确,立意新颖;2.内容充实,层次清晰;3.文面整洁,不得少于1500字!格式要求案例:题目:文章摘要:(不少于100字)主要观点概括(不少于300字)文章正文:(不少于1500)
1、“想问问这个孩子以后又继承财产的权利吗?”:这孩子有继承小乐父亲遗产的权利,如果小乐的父亲没有留下遗嘱的话。 2、“小乐的父亲帮小乐的舅舅做生意结果偷用了几十万来养女人,这要夫妻双方一起承担还钱吗?”: (1)如果小乐父亲是借职务之便“偷用”的话,涉嫌构成侵占罪;如果不是利用职务之便,涉嫌构成盗窃罪或是其他犯罪。 (2)如果小乐父亲偷用这钱构成犯罪:这债务就不是夫妻共同债务、而是小乐父亲的个人债务:只能用小乐父亲的个人财产偿还。 (3)但鉴于偷用的是小乐舅舅的财产;不管是夫妻共同偿还还是由小乐父亲一人偿还:只要还不上,亏的还是小乐舅舅,还不上时,小乐妈妈不会不着急的。 3、“还有包养女人还生孩子在法律上算犯了什么法律?”:要区分不同的情况: (1)如果小乐父亲与那女人在外又领了结婚证、或者是以夫妻名义同居:就是涉嫌重婚罪的行为,触犯的是《刑法》;同时还违反了《婚姻法》中关于夫妻有相互忠实义务的规定,属于违反《婚姻法》的行为。 而且:如果那女人明知小乐父亲有妻子还和他犯重婚行为的:那女人也涉嫌构成重婚罪。 (2)如果小乐父亲只是与那女人勾搭成奸或同居生子:没有又领结婚证或是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情形的,就没有触犯《刑法》、不构成犯罪,只是违法行为,违反了《婚姻法》。 4、“如果要告上法庭她的父亲有哪些罪?会判什么刑呢?”: (1)如果有重婚行为的:小乐母亲可以到法院告他重婚罪,如果那女人明知他有妻子的,可以将那女人也一起告;重婚罪的处罚是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依据是:《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2)如果没有重婚行为、只是一般的结婚生子:不构成犯罪、没有刑事处罚,只是小乐母亲可以此为由请求离婚、并在离婚时请求少分他财产,而且如果他是长期持续稳定与那女人同居的,还可以在离婚时向他索要精神损害赔偿金。 5、“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不让那孩子继承呢?”:除非让小乐的父亲留下遗嘱,声明小乐父亲的所在财产都不让那孩子继承,此外别无他法。 6、“该怎么解决啊·上法庭?”: (1)应先收集好小乐父亲“偷用”小乐舅舅几十万的证据。 (2)然后和小乐父亲谈判:如果他能按时归还这笔钱,就先让他归还,能还上多少算多少。还完钱后再算其他的账。 (3)如果他已经挥霍、还不上了:让小乐舅舅立即向公安报警,请公安立案追究他侵占或是盗窃罪的刑事责任。 (4)在公安立案后,小乐舅舅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让他赔偿。 (5)小乐母亲可以在收集到他有重婚的证据后: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告他或他和她重婚罪;在重婚罪判决后再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离婚、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索要精神损害赔偿金;如果他没有重婚行为的:可以他有外遇为由起诉离婚,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请求少分给他;如果他和她同居的:可以在离婚时索要精神赔偿金。
希望对你有帮助 有关我国《婚姻法》中损害赔偿制度的几点看法 内容摘要:《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确定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使法律对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更进一步,使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判有了法律的依据,使我国婚姻家庭立法有了进一步的完善。但是该制度在实践操作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对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显得不足。本文就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基础,确立的意义,损害赔偿的要件,适用条件,赔偿义务主体的范围,以及实际操作中的归责原则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和探讨,并提出了一些现实存在的问题及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关键词: 婚姻的契约本质 损害赔偿 婚内损害赔偿 举证责任 (一)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 有学者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源于民法上的侵权损害赔偿。对破坏婚姻关系的行为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责任,依照侵害名誉权的法律处理。也有观点认为应将破坏婚姻关系认定为侵害配偶权的民事责任,实行精神损害赔偿。 本文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在于婚姻的契约本质。 长期以来,我国并没有采用婚姻契约理论,传统认为“婚姻是男女双方精神上的结合”,“爱情是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的”,更有反对确立婚姻损害赔偿的人士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了婚姻的伦理本质,并使婚姻关系商业化,法律解决道德的问题是不妥当的等等。总之,这是因为对婚姻的本质存在不同看法而导致的不同结论。婚姻是男女双方为共同生活的目的而依法结成的以人身和财产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种民事契约。就是说,婚姻的本质是一种契约,而契约不仅强调权利,更强调自由。因此,我们可以说,婚姻意味着自由。法律上的婚姻自由制度的根据就是契约自由,包括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我国采取结婚登记主义,这说明,婚姻契约的缔结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进行。它的内容就是夫妻双方各自所享有的婚姻权利和各自所应履行的婚姻义务。这种权利义务包含了人身和财产两个方面;而且婚姻当事人可以选择离婚来解除这种权利义务,即婚姻契约的解除。以上内容均可反映出婚姻的契约本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就是从婚姻救助措施的角度来反映婚姻的“契约”本质的。我国修改前的婚姻法并无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而国外立法却早在几百年前就确立了这项制度。如1791年法国《宪法》、法国民法典、墨西哥民法典均确立了这项制度。 婚姻的“契约”本质在我国长期受到禁锢,在封建社会,夫妻双方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是极不平等,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长期以来,人们似乎承认婚姻是一种契约,仿佛就是把婚姻看成了一种可耻的交易。所以应当说,这种理念回避了婚姻关系的本来面目,也限制了婚姻自由原则的贯彻和实现。所以妇女在婚姻关系中基本没有什么合法权益,当婚姻关系破裂时,更谈不上合法权益的保障。近年来,随着民众“契约”理念的渐趋深入,有关婚姻本质的认识也越来越明晰。并且,这种认识已经反映到婚姻立法上来。我国现行的婚姻法正是基于婚姻的契约本质而确立了损害赔偿制度。尤其是《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过错方已经严重违反了婚姻契约之义务,理应承担损害赔偿之责任。 (二) 《婚姻法》确立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2001年,我国《婚姻法》确立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 (1)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目前社会形势下保护婚姻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有利于警示、惩罚重婚,姘居,通奸,婚外恋,家庭暴力等过错当事人的行为。 (2)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公序良俗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在人们对包二奶,通奸,姘居等行为日渐麻木漠然 ,社会风气日渐沦下的今日,用法律的手段,来提高道德的认识是必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树立崇尚法治婚姻,道德家庭的理念。 (3)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加强民事法律制度的需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之一,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4)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司法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需要,也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从以往的司法实践看,由于我国原婚姻法没有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只能按照分割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来操作。但是在财产很少甚至没有财产的情况下,该照顾原则根本无法适用,无法给予无过错的受害方以公平合理的保护;同时使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和制裁。因此,让司法有法必依,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至关重要。 有反对该项制度建立者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婚姻的伦理本质,而惩罚第三者是用法律干涉私人的感情世界,道德问题不能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并且容易造成侵犯他人隐私,捉奸成风的不良风气,司法介入婚姻过错的调查,取证困难,诉讼成本高,操作难等等。笔者认为,婚姻关系是建立在夫妻双方感情的基础上的,但婚姻关系的维护除了需要感情的积极因素,也需要法律制度的介入。婚姻法有伦理道德方面,但更多的确实法律制度。如前所述,我国采用结婚登记主义,婚姻这项契约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缔结。它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巨大利益,更涉及社会利益,理应受法律的严格保护。调查难,诉讼成本高不能成为反对立法的理由。三峡大坝水利工程难、成本高,为什么国家还要建设?因为它建成后的社会效益可观。那么建立婚姻法上的损害赔偿,其社会效益,也具有长远的精神效益! (三) 损害赔偿的要件 根据婚姻法的立法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几点: 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过错。这是损害赔偿的主观方面要件,即要求一方主观有过错。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无过错,则不承担赔偿责任。 行为具有违法性。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行为要件,即过错方的行为违反了婚姻法的规定或婚姻契约对婚姻义务的要求。 请求权人有受损害的事实。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后果要件,即享有请求权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具有损害事实,包括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事实上,也只有当无过错一方有损害事实时,才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需要强调和补充的是:通说精神损害赔偿要有精神损害的事实。因为精神本身是抽象的,又要求它用法律所要求下的事实状态表现出来更难。在学理上为了解决精神损害存在的客观性,有学者和实务者将精神损害分为“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和“证实的精神损害”。所谓“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又称“形式上的精神损害”,只要受害人有举证侵害人的侵权行为明确存在的表现形式,依一般的认识水平,相信受害人确实存在遭受精神损害的事实,法律则推定这个损害的真实性。所谓“证实的精神损害”也称“实证的精神损害”,法律不能推定受害人是否存在精神损害的真实性,受害人必须举出证据加以证明是否存在心理上,身体上,精神上受到损害。笔者认为:通说要件所述的精神损害的事实应理解为是“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只要有侵害婚姻家庭的危害行为的存在,即推定受害方存在有精神损害而无须再辅以证据加以证明。 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具有因果关系。这是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要件,即违法行为与无过错一方的损害事实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四) 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 文中在阐述中一直强调婚姻的损害赔偿,而非离婚的损害赔偿。这正是本文的重要观点之一——确立独立的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支持婚内损害赔偿。 《婚姻法》第46条适用的条件是“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应该理解为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提起确定了一个前提条件吧? 那么,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不要求离婚就不能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么?难道说无过错方要想得到赔偿就必须以离婚为代价么?笔者认为,这种规定,无疑使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形成了一种“强行配售关系”,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想主张损害赔偿,那么离婚便成为了一种“强制搭配品”,否则损害赔偿就无从提起。然而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两种本质截然不同的权利。离婚请求权是基于婚姻关系的破裂而主张夫妻关系的解除,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基于违背婚姻法所规定的义务的违法行为而主张受损权益的法律保护。因此,应将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一项独立的请求权,取消以离婚为前提的限制,支持婚内损害赔偿的请求。也许有人认为这种赔偿没有什么意义?判来判去都是一家人的财产。但笔者认为,这样界定是有意义的。它可以整体提高人们对家庭、对婚姻义务的重视,起到警示的作用,而对有过错一方进行惩罚和教育,即体现了法律的威力所在,又有利于过错方悔悟,使其“回头是岸”,促进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如果一定要以离婚为代价,对无过错一方也是不公平的。并且对于这种因婚内赔偿无过错方所取得的财产或财产权利亦应认定为其个人财产。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其稳定与否,在一定因素上关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如果确立这种独立的赔偿请求权,从长远的角度看,其社会效益,精神效益都是可观的。 (五) 损害赔偿义务主体范围的界定 《婚姻法》第46条,在责任主体上界定模糊。从条文分析,损害赔偿义务人限制在夫妻双方的范围之内,这使得受害人在权利保护上受到影响。实际上,是免除了有过错的第三方的连带责任。无过错方可否向“第三者”主张赔偿呢?笔者认为可以。第三者介入他人的婚姻,是对现行法律保护的婚姻制度的破坏,同其他的违法行为的本质是相同的,而不仅仅只是道德问题,法律必须做出否定的评价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制止,制裁。因为配偶一方与婚外第三人重婚、姘居、通奸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过错方有错的同时,第三者也大都有过错,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不过,无过错方不应在离婚诉讼中向第三者主张权利而应另行提起侵权之诉;如果像本文第四点所述的,允许婚内赔偿的话,无过错方则可以以有过错的配偶和第三人为共同侵权人提起侵权之诉。有的专家、学者称“惩罚第三者有可能导致捉奸成风,司法上难以操作。”笔者认为:只要第三人插足于他人家庭并有重大过错,如重婚、姘居、长期通奸,及导致他人离婚的就应受到民事制裁,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亦不免除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追究第三人责任体现了一种立法价值取向,维护公序良俗。当由道德约束的问题超越了社会文明的底线,则需要法律来维持它的正义和标准。如果法律对第三者的重大过错视而不管,仅对离婚过错方进行惩罚,将达不到法律所预期的预防,警示及教育,惩戒作用。而且设立向婚姻损害第三方主张损害赔偿的制度也是多数国家法律的通例。 (六)婚姻损害赔偿制度在举证责任方面存在的问题 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权主张损害赔偿的是“无过错方”。其意味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以过错为归责的最终要件。这样举证的责任就落在了无过错的受害一方。在单纯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下,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者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对这一证据的采集要求在婚姻家庭领域存有相当的难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为若干解释)第二条规定:“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权利主张者如何来证明配偶与婚外异性该种关系的持续性、稳定性呢?有些权利主张者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雇佣私家侦探或干脆自己充当起私家侦探的角色,期望借助这些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请求。但往往会由于收集证据材料及运用证据不当而引发权益之间的冲突。譬如,将捉奸照公布于众,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将同居的事实大肆渲染,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等等。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权利主张者根本无法提供此方面的证据材料。在种种状况下,一味地实行谁主张谁举证,便可能导致该种局面:由于证据的不足或缺乏证据,权利主张方的请求权实现不了,应承担责任的一方则可逃脱法律的惩处。法院的法官明知存有侵权的事实却苦于证据的缺乏而无法对被侵犯的民事权益给予相应的民事救济。在该种局面下,损害赔偿制度确立的立法价值,其所透析的立法精神便荡然无存。 笔者认为:适当适时适地地采用过错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会加大受害方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 如果可以这样操作,那么有相当一些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我们主张,无过错责任或者特殊侵权场合,我国民法应借鉴法国的经验,侵权人侵害自然人物质性人格权,无论侵权人有无过错,均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换言之,在受害人之物质性人格权遭受侵害,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场合,可以适用过错责任,也可以适用无过错责任。正由于过错推定是从保护受害人利益考虑而产生的,其主要目的是对受害人提供救济, 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也应该将过错推定原则引入到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损害赔偿制度中。例如在重婚、与婚外异性同居等情况下,无过错方要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原则,由过错方对其对精神损害的后果没有过错进行举证。 正如本文前面所述,“法律视婚姻仅为民事契约”, 确立婚姻法的损害赔偿制度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更何况婚姻家庭关系是感情色彩非常浓厚的民事法律关系,它具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复杂性,会使婚姻家庭领域随时可能出现法律所预料未及的新情况、新问题。过错推定原则也会有助于对此类婚姻家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及时的调整。同时,也加大了对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 综合前六方面的论述,笔者在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方面存在了以下的看法及建议: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确立这项制度是我国目前婚姻家庭观念“世风日下”,恢复道德伦理的公序良俗的需要;对于婚姻法中的精神损害应理解为“名义的精神损害”为宜;损害赔偿不应局限在离婚条件之下,亦应及于婚姻持续的过程中;损害赔偿的义务人应包括有过错的配偶一方和第三人(权利主张者以何名义诉之在所不问);适当适时适地的采用过错推定原则来加大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 参考文献: (1)王利明 主编 《民法侵权行为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王利明 主编 《民商法研究》 (3)林秀雄《婚姻家庭法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李银河 马忆男 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 (5)关今华 主编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与评算》 (6)杨遂全《新婚姻家庭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7)杨大文主编:《亲属法》,法律出版社 (8)李绍章:《点评新婚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