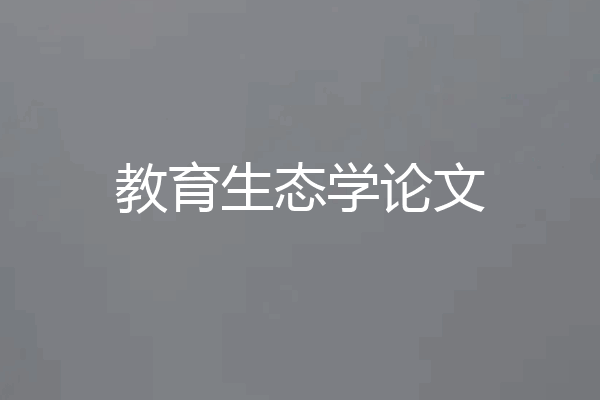上岸滑小稽
上岸滑小稽
教育生态学是一门运用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研究教育现象的科学,但不是把生态学的原理硬套到教育上来,更不是只从生态学中借用一些概念、术语。教育生态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研究具体的教育情景、教育问题。“生态学”一词最早是由博物学家索罗(Thoreau,ND)于1858年提出的。但是,它的内涵一直不确定,直到1868年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Haeckel,E)首次为生态学下了一个明确定义后,生态学在植物生态学(plantecology)和动物生态学(animalecology)领域才有了快速发展。现在,学术界对生态学较普遍的解释是:“研究有机体或有机群体与其四周环境的关系的科学。”生态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生态系统”。所谓“生态系统”是一种有边界、有范围、有层次的系统。任何一个被研究的系统都可以和四周环境组成一个更大的系统,成为较高一级系统的组成部分,而且,它本身又可以由许多子系统或亚系统构成。它们相互依存、互为因果。而且,各子系统或亚系统之间以及子系统与母系统之间也同样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业的发展、人口的增长,教育事业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教育的内涵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校教育,教育与整个社会的关系日益密切和丰富,并且贯穿人的一生。在美国,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崛起与普及,大大地改变了美国的家庭教育,从而也改变了美国的公共教育。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需要以一种全新的观点来审阅教育,而用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来研究教育问题则是人们的选择之一。1976年,美国教育家、前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劳伦斯·A·克雷明(Cremin,LA,1925-1990)在其所著《公共教育(PublicEducation)》中率先提出教育生态学(ecologyofeducation)概念。克雷明首次以生态学的角度提出关于教育的新定义:“我把教育看做一个审慎的、系统的和通过不断努力去得出或唤起知识、态度、价值、技能和情感的过程。”[1]。在克雷明看来,“教育”主要是指人们“有目的、有计划地”改变自己或他人思想、行为方式或情感的行为[2]。也就是说,“教育是通过周密的、系统的和持久的努力来传播、激发或获取知识、态度、价值、技能和情感;教育是由这种努力所产生的所有结果。”克雷明认为,这一定义具有以下特点:生态学原本是研究生物体与其栖息环境之间辩证关系的科学,而教育生态学的理论基础就是“相互作用论”,即各种教育机构之间以及与整个社会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考察教育问题时必须坚持生态学思考方式,即全面地、有联系地、公开地思考。教育生态学把教育看成一个有机的、复杂统一的生态系统,强调教育与环境之间、教育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过程及相互影响和相互适应的关系。 我国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到今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实践中还存在许多现实的问题。对同一个现象和事物用不同的视角去研究,无论对事物本身还是研究方法都很有意义。从生态学的视角审阅现代远程教育,也许就会找回现代远程教育长期缺失的本质:关注人的生命。本文试图从教育生态学的视角分析现代远程高等教育,将现代远程高等教育视为一个生态系统,具体分析其系统组成、影响因子、现代远程教育生态系统的生态平衡及相互关系,希望对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发展提供一点有益的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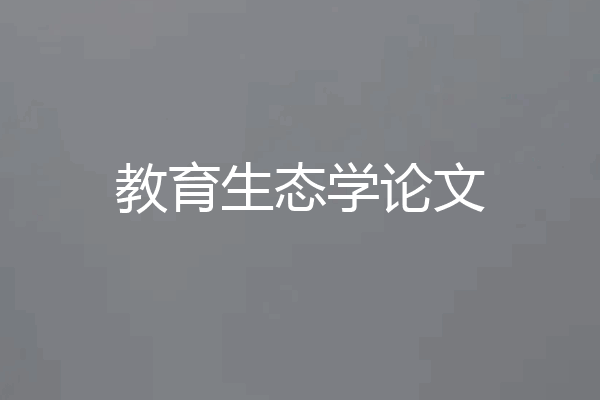
维护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对策比较 针对我国西部草原地区的过度放牧现象,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如下治理方案: 第一,政府干预或者说政府向牧民征收牛羊税。例如,在2000年上海举行的一次名为“走经济全球化发展道路:中国在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学术会议上,华裔加拿大经济学家徐滇庆教授便呼吁,中国政府应征收牛羊消费税。据他认为,把从牛羊肉消费中征集来的税收的一部分用于帮助农牧民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另一部分则可用于解决政府帮助农牧民转向其它产业所需要的财政经费来源。不过在我认为,对牛羊征税虽有理论或法律依据(即便国家是向牧民征税,也有依据。因为在我国的法律中,草原资源的产权被界定为属于国家所有,作为产权主体,国家显然有权力向牧民征收牧羊税),但是,在我国真正实施征税政策还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对牛羊课税的经济学含义即移动牛羊产品的供给曲线,税收的增加将促使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这一过程必然带来均衡点的移动以及牛羊产品价格的上升和均衡产量的减少。即使是对牛羊征收消费税,最终后果也可能会加重牧区人民的经济负担,严重的是将可能导致牧民失去生活的来源。特别是在牧民没有其它就业渠道的前提下,税负的加重无疑会使牧区人民的脱贫致富速度减慢,甚至还会使牧区人民陷入生存危机的困境之中。 具体说,如果消费牛羊产品的消费者是不受宗教和习俗制约的非少数民族人口,那么,牛羊消费税的征收以及客观存在的替代效应将可能改变其对牛羊肉产品的需求,即需求曲线的斜率会发生改变,需求曲线将可能变得较为平缓一些或更富有价格弹性这一结果将是:因供给减少所导致的价格上升不仅不能增加牛羊产品提供者的收入,反而会导致牛羊产品提供者(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下降。 另一方面,如果消费牛羊肉的消费者是那些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那么,受消费习俗或宗教因素影响,他们对牛羊征税的反应将是不会明显改变其需求曲线斜率,这时,西部少数民族消费者所面临的问题将是不得不分担更多的税收。至于西部地区牛羊产品的生产者则会因均衡产量的减少而使实际总收益下降。尽管政府税收的增加可以用于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方面,但是“双退双还”措施在近期所造成的农牧民直接收入的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总之,征税不仅会通过加大牛羊生产者的成本、削弱牧民的市场竞争能力而降低牧民的收入;而且会增加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消费者的生活费支出;此外,还会导致“消费者剩余”的无谓损失。因此,在不能给牧民提供其它有效的生活来源渠道之前,加征牛羊税对原来就贫困的广大西部地区来说是不可取的(至于以行政手段禁止牧民养羊更没有道理可言)。 第二,重新界定草原的产权。即明确草原的产权主体,或者允许土地(草原)自由贸易。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2000年参观江苏企业改制时,曾建议通过“进一步明确土地的产权”来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主张改革土地(或草原)资源产权的经济学家依据现代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安排,具有节约费用的作用,它能以低费用的方式解决人们在使用稀缺资源(如草地)中的冲突。换言之,按照产权学派的观点,将草地分给牧民私人所有,将会促使牧民充分关注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过度放牧现象也就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然而我们认为,在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无论是对土地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还是实行“自由贸易”改革均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重大障碍。 既然“禁止牧民养羊”的行政干预办法、“征收牛羊税”办法以及“进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办法,在解决西部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上或不可取,或在近期内不具备可行性,因此,我们提出“人口迁移或减少牧区人口数量”的对策主张。 实际上,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根本原因乃在于人口过多。按联合国沙漠会议规定,干旱区每平方公里土地负荷人口的临界指标为7人,半干旱区为20人,然而我国西部地区诸省区的情况如何呢?大多数地区的人口都超过了此临界指标。以宁夏为例,目前,其山区人口较1950年代初期增长了250万,人口超过临界指标2.3—2.4倍。必须看到的是,在工业化与现代化没有完成的传统社会或落后地区,过多的人口数量或过快的人口增长必然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和草地的过度放牧,因为,在工业化不发达的前提下,草原地区的人民只有依靠增加牛羊放牧数量才能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目前宁夏山区的牛羊数量较1950年代初便增长了274%,牲畜超载2.3倍。(9)可见,草原牲畜放牧的超载,首要原因是草原上人口数量的超载。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考虑的对策就应该是设法减少西部牧区的人口总量,而不能象现在一些地区那样简单地“消灭山羊或不允许牧民养羊”。而且从理论上讲,西部地区牧民的减少或牧区人口的转移其实是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现代化进一步推进的必然规律,人口的转移不仅是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客观需要;而且是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