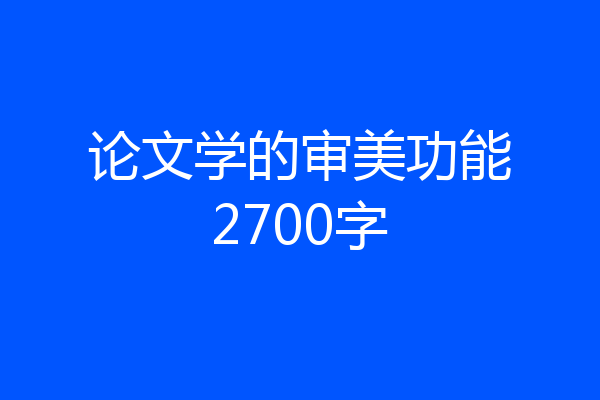silence_lisa
silence_lisa
文学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只有通过文学的审美作用才能达到。读者阅读文学作品首先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这种愉悦与满足的过程包裹着情绪上感觉上的快感与修养,这就是说文学具有审美意识形态性质的双重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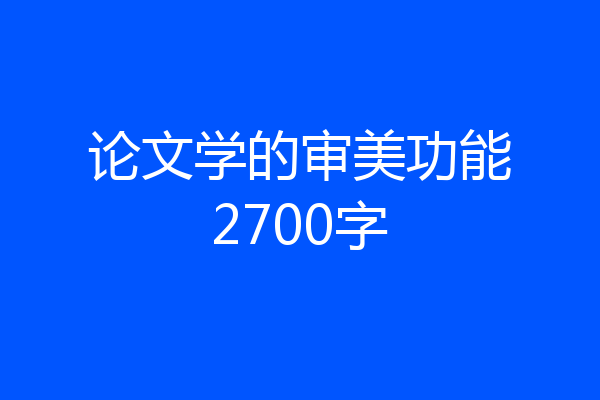
文学的审美功能包括文学的审美认识功能,审美教育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 自古以来,对究竟什么是文学,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古人说“诗缘情”、“诗言志”;现在有人说文学是一面“镜子”,反映社会现实,有人说文学是游戏,给人带来娱乐,也有人说文学的意义在审美,倡导为艺术的文学。其实,上述种种说法,涉及的内容都不是文学本质,而是功能。世上能对其它事物产生影响的事物,都具有一定的功能。功能是事物的属性,在事物各种属性里,它属于潜在的能力。说“诗言志”,或者“诗缘情”,其实是说诗能够表达志向,能够抒发情感,但它不一定非得表达志向,非得抒发情感,它只是具备了类似的功能而已。本质则不然了,本质不是事物的属性,而是核心,决定事物的性质,本质和功能不可同日而语。文学具备某种潜能,就有可能达到某个目的,或者呈现某种形态,而它的本质决定了它是什么又不是什么。 功能不能取代本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许多文学本质之争,其中的大部分,其实都是功能之争。文学有许多功能,其中没有主次之分。文学的诸多功能决定了文学的多元,文学的多元决定了文学的多义,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如此纷繁灿烂的文学现象。如果把其中之一定义为本质,就是在它们中间分主次轻重--文学的根本意义取决于它的某个功能,而其它的功能只能隶属于它。于是就有了在文学内容上的题材大小和意义大小之分。许多年前,我在校园书店翻过一本当时的文学理论书籍,我只看了看目录,没有细读。书的作者列举文学几种常用功能,例如反映社会生活、抒发人的情感、教育作用、审美作用,给它们分别命名为本质、特质和特征。用类似术语命名功能,等于说给它们排座次,老大,老二,老三--认为它们在文学中起的作用各不相同。至于其它文学功能,就更等而下之,连“特征”都捞不上。这种做法聪明,但不可取,因为事实并非如此。虚的不说,就说具体运用吧,会影响对作品的评价,那些不能体现那所谓的文学本质的作品,哪怕再优秀,也只能算二流之作了。举个例子。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记》 诗人写自己站在高台上,望望天地,想想古今,然后感伤地落下眼泪。它的内容就是如此简单,无论从“言志”或“缘情”上看,都无法表现充分,从反映社会生活的角度来看,更是淡如云烟了--然而,它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好诗,即使在唐诗里,也属不可多得。它的意蕴不可能与文学的根本意义无关。一部公认的传世之作,其内容与公认的文学本质若即若离,另一部作品则直接体现了公认的文学本质,而世人却又公认它不如前一部好,这种现象如何解释?把文学的某个功能提升到本质的高度,确实会出现类似令人尴尬的情形。白居易最优秀的诗理应是《长恨歌》和《琵琶行》,但在从前流行的几种文学史里,评价最高的是新乐府。编者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反映社会真实,当时属于阶级社会,阶级压迫是普遍现象,白居易的新乐府涉及了这方面内容,因此文学价值最高。类似的例子还有。如果认为娱乐性是文学的本质,《红楼梦》自然不如《西游记》。我上小学时读《西游记》,上中学时读《红楼梦》,读《西游记》时津津有味,读《红楼梦》却苦不堪言,虽然已经比读《西游记》时年长许多。如果改变一下文学的价值观,情况又不同了。无论哪一种功能视为文学的本质,《红楼梦》的价值都高于《西游记》。(我在写此文时,发现“红楼梦”作为一个词组,已经被收入电脑词库,说明它已经属于常用词组了,而“西游记”在词库中则找不到。)把文学的功能定义为本质,任何一种可能的价值取向,都必然导致评价的偏颇,不是朝这一方面偏斜,就是朝另一方面。 必须跳出视功能为本质的争论怪圈,对文学有一个新认识。我认为文学应该分成两类:一类是作为形态的文学,另一类是作为生命的文学,前者指文学作品,后者指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作为生命的文学,通俗地讲,也就是人的文学情怀。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每个人都有。你见到美的事物,内心受到感动,那就是你拥有文学情怀的缘故。文学作品来源于你的文学情怀,有了文学情怀,才能创造有血有肉、有生命活力的文学。文学的生命力来自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