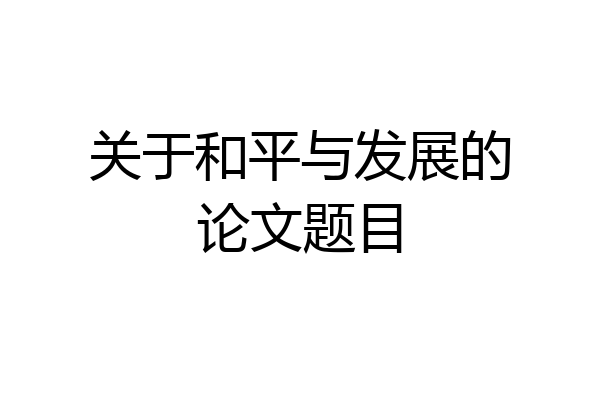淮安
淮安
在人类文明史上,大国崛起往往伴随血腥和战争。一个日渐发展起来的中国,将会展示出什么样的形象,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世界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重申:“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我们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我们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推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反对一切形式的。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这些论述鲜明回答了中国在国际上走什么道路的问题,阐明了中国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和方向,既坚持了中国外交方针的一贯原则,又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申明了中国对当今世界一些重大问题的基本态度,更是对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的响亮回答。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是我国外交方针的一贯原则。当今世界尽管存在着的激烈竞争,全球经济失衡的深刻矛盾,单极和多极的激烈较量,形形色色的局部战争,以及、环境污染等各种各样的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但是,从大局、主流、根本趋势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在外交实践中,中国从来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国际合作的坚定力量。党的十七大报告再度申明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顺应时代潮流,切合时代主题,符合我国追求和平发展的一贯原则和立场,有利于澄清外界的各种无端猜测和疑虑。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主题是发展。中国的发展战略归结起来就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这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和平发展是中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和方向在对外领域的自然延伸,是中国国家本质在国际上的自然展现。中国人民高度珍视和平的价值,在集中精力建设自己国家的同时,把争取良好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作为保障国家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的宗旨,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持以积极负责的态度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积极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追求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和平发展道路体现了这样的宗旨和追求,充分表明我们是始终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处理问题的,是在兼顾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决定我们的发展道路的。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始终不渝的战略选择,贯穿我国对外工作各个方面。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在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我们将继续同发达国家加强战略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我们将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的地区环境。我们将继续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深化传统友谊,扩大务实合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和共同利益。我们将继续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我们将继续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加强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团体对外交往,增进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这些部署充分体现和平发展精神,表明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携手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坚强决心。 和谐世界”理念与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西方国家对华采取敌对封锁政策,周边国家对新中国心存疑虑,如何实现中国与不同制度国家间的友好交往,突破帝国主义的外交封锁,成为新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定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准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在亚非会议上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1954年6月底,周 总理应邀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分别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举行了会谈,并在会后的联合声明中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双边关系的原则。1955年4月,在印尼召开了有29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会上少数代表发言攻击新中国。周总理在发言中着重阐述了“求同存异”的思想。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不是来吵架的;是来寻求共同的基础,不是制造分歧的。“求同存异”就是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放在一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找共同点。周总理的讲话得到了与会代表的广泛赞同。最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写入会议公报。自那时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国处理同一切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出现在中国与160多个国家的建交公报中。中国还积极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是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核心;平等互利、共同发展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核心。中国领导人根据形势发展,不断丰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涵。邓 小平同志依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与时俱进,提出了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主张,强调既要着眼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要尊重对方的利益。他还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以及通过“”解决一个国家内部某些问题的伟大创举。“和谐世界”理念注重国家间的对话、协调与合作,强调国家间的平等、相互依存和遵守国际规则的重要性,体现了和平共处的意愿。它实际上高度概括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是对五项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和谐世界”理念与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脉相承作为一个,新中国从成立之日起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冷战时期,由于面临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国通过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采取与一些大国结盟或准结盟的策略,反对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冷战结束后,中国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推动自身和世界的发展放在维护自身安全与世界和平同等重要的地位。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陆续提出了新安全观、新文明观、新发展观及“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在追求自身发展和强大的同时,努力实现与他国和平共处、共享繁荣。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和谐世界”新理念的目标──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是对我国外交政策宗旨的继承和升华。在和谐世界中,各国内部的事情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由各国平等协商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享有平等参与权与决策权。各国互相尊重,平等相待,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将自身的安全与发展建立在牺牲他国利益基础之上。“和谐世界”新理念的这些主张,是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集中体现。“和谐世界”理念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创新由于各种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曾长期游离于国际制度之外,并对战后国际秩序抱有批判、反对的意识。在外交实践中,中国扮演着革命者的角色,试图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秩序。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融入现有国际机制,特别是各种国际经济组织,搭上经济全球化的列车,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参与多边机制的增多,中国对多边机制及其运行规则逐步有了全面的认识,对国际秩序的认识也逐渐发生变化,从现有秩序的批判者向有保留的认同者、建设性的融入者转变。近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尽管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包含着大国政治、维护西方发达国家政治的不合理成分,但也存在尊重各国主权和人权、照顾发展中国家及对大国力量进行制约等积极因素。当前国际秩序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合理的一面正在受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冲击,而不合理的一面未能得到改变。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改革的方式使其更为公正合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希望作为一个建设性的合作者,通过积极参与制定、修改国际规则,参与国际,逐步改正其中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使之能够反映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利益。近年来,中国在联合国改革、朝核六方会谈、东亚区域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建设、反恐、防扩散等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已成为世界体系的建设性参与者、国际矛盾的积极协调者、周边秩序的务实塑造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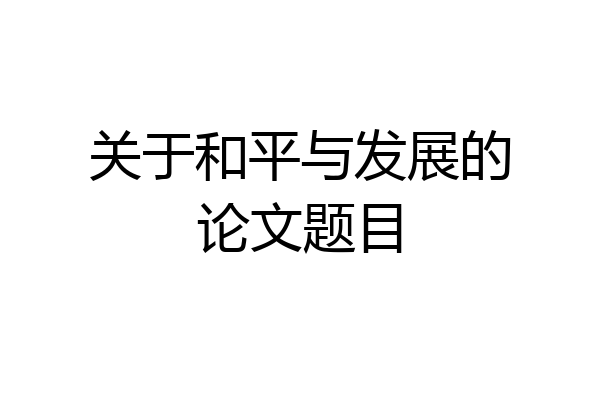
一.逼近眼前的生死抉择 和平是人类最持久最朴实的追求。和平意味着生存的机会。人只有在和平的状态下才能正常从事一切有利于生存、发展的建设性活动,生命的尊严也只能在和平状态下才有条件得以普遍展现。然而对和平的持久追求本身也表明了人类长期被战争所伴随的不幸事实。 战争,是人类自己发明出来的最大灾难之一。无论战争因何而起,它都不仅是手执武器的人互相残杀,更是平民的无辜受难。战争造成的惨烈后果——生灵涂炭、村庄被焚毁、城市成废墟……——从来就是要由人民来承受的。对于人民来说,战争意味着动荡、恐怖和死亡阴影。但战争却总在发生,人民防不胜防。 在人类历史上,和平与战争犹如一对连体儿。一方面,战争手段的运用之普遍和经常,使它几乎成了人类一种常规活动。阿里斯托芬曾通过剧作《和平》发出感慨:“一直在将你期待,一直在将你找寻;非同寻常的期待,非同寻常的找寻。”这正是频繁的战争造成和平稀缺的一个佐证。另一方面,人们从未停止过创造和平局面的努力和在战争的间隙中创造生活的努力。在和平与战争的交替中,是创造与毁灭的悲剧性交替。如果说过去这种悲剧性交替中,人类还可以在战争的间隙中重建生活,如今当足以毁灭整个世界的生化武器、核武器被发明出来,诱发战争的因素又愈益增加,核战呈一触即发之势,“生存还是毁灭”这个似乎过于形而上的问题已经逼近眼前,成了全人类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在毁灭性的核战阴云笼罩下,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存在于制止战争和争取持久稳定的和平的努力之中。 二.和平与反战的思想探索 战争使人类历尽苦难而期盼着和平。但持久稳定的和平有赖于许多条件。对战争这一横贯全部人类史、称得上人类常规的活动进行反省并对诱发战争的原因进行探究,有助于为和平创造条件的努力。 在人类思想史上,和平与战争是一对永恒主题,探究从来没有停止过,所涉内容,十分广泛。尤其人们熟知的那些杰出思想家深具人道主义精神,他们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但作为思想家,他们不是简单地赞颂和平谴责战争,而是致力于对战争根源的挖掘和对战争性质的剖析,致力于探索摆脱战争的可能性和持久和平得以实现的条件,阐释的思想对于我们理性地认识战争和争取和平有着重要启示。 1.战争根源探究 思想家们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性等多方面对战争根源作了探寻,揭示了贫穷与战争之间存在着联系,种族、文化、宗教信仰冲突往往成为引发战争的因素,战争与人的攻击性和冒险精神,特别存在于某些人身上强烈的征服欲和野心有着关联。但我认为对战争根源所作的最重要探寻,是揭示了专制政体与战争的内在关系。这一思想在西方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四百多年前苏格拉底就指出专制僭主通过挑起战争使人民需要一个领袖。稍后,亚里士多德把专制政体判定为要靠战争来维系稳定的政体。十八世纪,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揭露了专制统治者和教权主义者为着权欲、为着征服、为着所谓主义把人民推入战祸的真相,并指出对外的战争和征服与对内的独裁专权相互支持这一事实。当代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则不约而同指出近现代一个事实:专制国家不仅屡屡到处挑起战争,而且彼此之间也经常爆发战争,哪怕意识形态相近甚或相同也难免兵戎相见,这与战争从未发生在民主国家之间呈耐人寻味的反差。这一反差对战争是专制政体的内在本性提供了颇为独特且有力的证据。 专制政体之成为战争根源,乃因作为这种政体特色而存在的专断权力在根本上处于无制约无制裁状态以及这种政体本质上的不正义和扩张、征服倾向。事实上,权力占有者对内的不义统治本身就酝酿着内战。对外,由于专制政体的权力来源、是否进行战争的抉择方式和取得战争经费的方式与共和政体判然有别,两种政体下民意的分量和人们生命的分量更是迥然不同,这使得战争决定如康德所指出的,在共和制下是最艰难的决定,但对专制者来说,却可以成为“全世界最不假思索的事情”。①所以,一旦实力具备或者以为实力具备,战争几乎是必然的选择。而对发动征服战争的人来说,战争可能带给他们的东西与带给人民的不一样。胜利带给他们的是财富、土地、荣耀和统治权的扩大,为取胜所必须付的代价却要由人民来支付;如果战败,战争发动者不必为后果负责,其惨烈后果将全部转嫁给人民,尽管人民从来没有机会对是否进行战争表达意见;如果面临灭顶之灾,“绑架”整个国家作“人质”,甚至拉全体人民作陪葬——这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不少见。专制体制下权力与责任之间荒唐的不对称决定了使战争永久化是形形色色的专制统治者的共性。 但专制制度成为战争根源还不仅在于上述原因,还在于这种制度具有把某些作为战争发生可能性的因素刺激、挑逗起来引向战争的倾向。其实,无论人性中固有的攻击好斗性、冒险性,还是某些人的野心和征服欲,或者种族、文化、宗教信仰差异,都并不必然使人走向战争,它们都只是一些潜在的可能。但专制制度注定要把这些潜在可能变成现实的战争因素。因为这种制度既给了统治者凭借权力强制性驱赶人民上战场卖命从而使他们的野心和征服欲得以兑现的条件,又使他们可以利用欺骗、煽动和暴力思想的灌输使人性中原本可能通过富于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方式释放的攻击性冒险性采取暴力的破坏性发泄方式。至于在不同种族、文化、信仰之间制造隔膜、挑起仇恨,加深误解和冲突,把差异变成战争的理由,更是专制国家惯用手法。 关于专制制度与战争的关系,专制制度导致战争是问题的一方面,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战争对民主国家的自由构成最大威胁。威胁不仅来自外部专制国的战争倾向,还因为战争将不可避免地会破坏民主国家作为人民自由之制度性保障的权力平衡。这就是托克维尔指出的那种危险:战争将不可避免地使参战的民主国家把对一切人的指挥权和对一切事物的管理权强制性地集中到行政当局。而一场持久的战争则势必把权力向行政当局集中的危险趋势固定下来。 战争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多侧面关系,提示了避免战争、实现持久和平的最重要思路。 2.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 要避免战争、争取和平,需对战争本身抱理性态度。为和平而谋划的思想家们并不一概反对战争,他们中不少人赞成在某些情况下进行战争并为之辩护。最重要辩护是对战争作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区分。把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的,与对战争的谴责一样源远流长,而且不光众多思想家作这样的区分,一般民众也自发地倾向这种区分。尽管在“何为正义何为非正义”的问题上分歧重重,但人类还是逐渐取得一些基本共识,如:侵略战争、征服战争,出自压迫、掠夺目的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基于自卫,为保卫和平和家园、为了自由和尊严而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杰出的思想者就战争问题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所作的是非辨析推动了基本共识的形成。从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开始达百年之久的希波战争,对希腊人来说,不仅是反抗侵略,而且是一场为着捍卫自己的城邦制而与强大的专制帝国进行的殊死斗争。斗争的胜利使希腊的独立城邦幸存下来,并创造了对全人类影响深远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基于这双重的正义性,希腊哲学家、诗人们,包括深刻揭露了战争残酷性的三大悲剧诗人无不引以自豪并为之辩护。即使反战立场最鲜明,以一系列喜剧鞭挞讽刺愚弄人民、鼓吹城邦之间内战的政客的诗人阿里斯托芬也对希波战争中抗击波斯入侵者的勇士大加赞扬。世界各大宗教创立者都反对战争,但也认肯了自卫的权利,尤其基督教一些著名神学家,如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他们都对这类权利作过有力论证。阿奎那不仅从战争理由、目的等方面梳理了使一场战争具有正义性的条件,还通过指出暴君在臣民中制造倾轧和纷争是犯了严重的叛乱罪,为推翻暴政的行动作了辩护。在十七世纪思想家洛克眼里,战争状态是一种敌对和毁灭的状态,这种看法表明了对战争的反感,但他同时坚决反对为了和平让无辜者乖乖地任人施暴。在他看来,这种由强暴和掠夺构成的和平无异于要民众充当驯顺的羔羊,不加抵抗地听任豺狼咬断自己的喉咙。人道主义者雨果主张以博爱促进和平,向往不再有持剑的士兵、不再有国界,整个宇宙为一家的和平前景。但他坚定表示,决不要低头屈膝的和平、专制下的和平、王朝下的和平。1869年的洛桑和平大会上,雨果提出和平的首要条件是解放,并认为为此“也许还需要最后一次战争”。二十世纪初,法国社会党领袖饶勒斯就日益逼近的战争对社会党人提出了双重任务:当战火还只是遥远的威胁时,应该用斗争来防止战争,但危急时刻就应该发动捍卫民族独立的战争。至于投入正义战争的必要性,爱因斯坦以反纳粹的战争为例作了透彻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