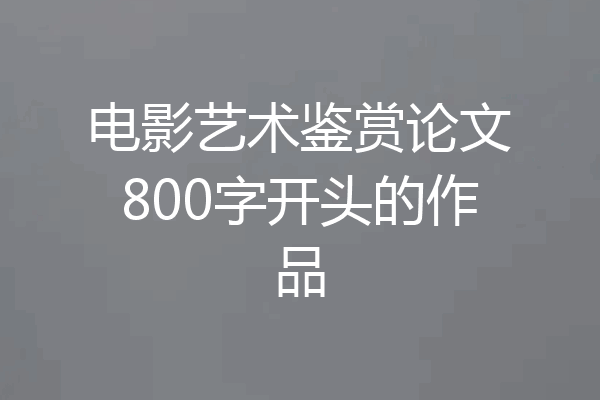sypgrzghb
sypgrzghb
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传世经典,自问世以来不断地被搬上舞台和银幕。电影人对这个故事颇为热衷,从早年奥逊·威尔斯(《公民凯恩》)版本到近期威廉·赫特(《大寒》)版本,在历时半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7、8个版本《简爱》影片的诞生,不同的代电影人在各自的作品中用自己的角度阐释对作品的理解,同时也推动了这部经典名著在全球的普及。1970年的乔治·斯科特饰演的版本历来被公认为是所有版本中改编得最恰到好处的——既忠实于原著精神,且故事结构更为紧凑,爱情主题更加突出。苍凉静谧的英国荒原,神秘诡谲的古堡,加上“老戏骨”乔治·斯科特(《巴顿将军》)的表演,将一个维多利亚时代哥特式的爱情故事演绎得凄美动人。乔治·斯科特的表演无疑是本片的一大看点,他的激情演绎使其他版本的罗切斯特黯然失色,其锋芒直逼早年的奥逊·威尔斯。而苏珊娜·约克外表沉静,含蓄内敛的风格也被评论界称为最接近原著简爱的精神气质。本片的主题音乐更是大手笔,它出自著名音乐人约翰·威廉姆斯之手。这一主题曲把本片的爱情主题推向高潮,更成为该版本的标签,至今仍在不同的音乐会上被演奏。 对于中国观众,这一版本的意义尤为特殊——它被无数次地制成录音剪辑,在全国各地的电台一播再播:它被制成各种版本的录音带,被“听迷”们争相购买,听这部电影着迷的人甚至比有机会看这部电影的观众还要多。对于出产了无数配音电影精品的上海电影译制厂,《简爱》堪称精品中的精品。在观众每一次选出的配音作品中,《简爱》无不位列三甲。它从台词翻译到演员表演,无不成就了一种典范。这是配音大师邱岳峰与李梓的颠顶之作,他们用声音拓展了新的表现空间,丰富了电影这一“视听”的艺术在听觉上的美好体验。邱岳峰塑造的罗切斯特,或愤懑,或柔情,或倦怠,或狂暴,无不让人动容。而李梓演绎的简爱在不愠不火的声调里展现出细腻的情感变化,或温婉,或坚定,也在更深层次上丰富了简爱人物的形象。他们的声音有表情,有形象,有情感,一寸一寸都是鲜活的。 本片是20世纪70年代初拍摄的小成本电视电影,虽然由明星乔治·斯科特担纲主演,但国外观众对其评价不高,在国外电影市场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力,是上海电影译制厂表演艺术家们的精湛技艺使得她面貌焕然一新,成为观众心目中外国电影经典之作。经过邱岳峰和李梓主配之后,多少观众为之倾倒,甚至有人在寒冷的冬夜刚看完这部片子步出影院,便满怀激情吟诵起罗切斯特和简爱的对白来。简爱的爱情观、价值观、人生观对不少女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孕育了一批中国式的女权主义者。大伙欣赏之余,还找来原著细细品读、比较,至今我还珍藏着它的CD录音剪辑。以前市面上充斥的尽是奥逊·威尔斯和琼·芳登主演的美国版,以及其它新版的《简爱》,而这次全美的倾力奉献总算让我得偿所愿了。 这是一部特殊的电影,观众可以闭上眼睛,倾听这来自灵魂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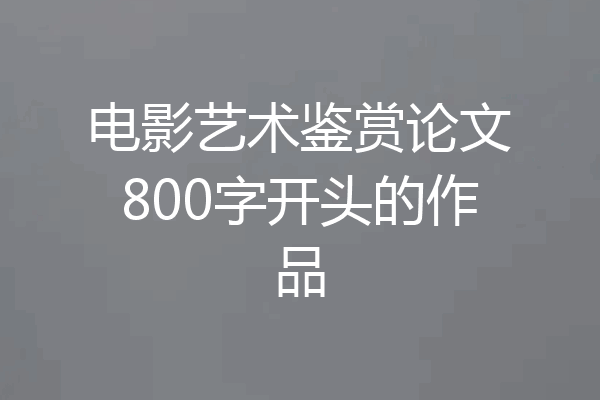
欣赏电影的话,你可以从剧情,拍摄手法,剪辑手法等方向进行赏析。
整个电影里,我只看到两个字:抽离。 从所有的生活中抽离,从所有感情中抽离,从所有欲望中抽离,从所有人际关系中抽离。 这部电影,某种程度上是一首诗。诗是什么?最纯粹的东西,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懂得其中的秘密,一种就是哲学家,一种就是诗人。前者从绝对的理性出发,知道了这个世界运转的规律,后者从直觉中出发,直接往最幽深的地方走。 所以,你现在知道了商业电影和最好的文艺片的区别了吧?商业电影刺激、煽情、百转千回,一部好的文艺片又是怎么样的呢?只是叙事,导演就是上帝,所有的人物都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他们有自己的性格、自己的语言,所有的故事都是他们自己的,隐然要跳出故事的框架,导演,就像上帝一样,冷漠的观察,从来没有喜剧或者悲剧的区别,他们就在那儿。 语言是多余的,从来就是。 从审美的角度出发,大概是朱光潜说:艺术的本质是诗意,即使是小说,诗意就像是花棚的家子,上面攀爬着无数的繁茂的花朵,而这些花朵,就是小说的故事性。故事,必须为本质的诗意的花架服务。 我们在《红楼梦》里大概看到过这种诗意,在米兰昆德拉小说里也看到过一些,不过忧伤了些,作者带了自己感情进去,在王小波的小说里也看到过诗意。不过即使是最最优秀的小说,都还必须借助于故事和情节来表现诗意,而直接用诗来表达的呢? 诗跟语言有关系,语言的断续存亡,直接影响了表达的准确,白话文时代的中国诗人,放到唐宋,最优秀的都变成了二流。而整个文学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世俗化的过程,诗、词、戏剧、小说。越到后来,越是通俗,诗意越少,不过受众却越多,决定艺术形式流行的,是受众最多的那一群体,而不是受众艺术水准最高的那个群体。 回到抽离。 人生于世,受到两个困扰,身体的欲望和外在的评述,倘若扔掉这两个困扰,人人将成为圣人。佛偈:脱下你的衣服!什么是衣服?身体的欲望就是衣服,这是内在的困扰,外在的困扰,则是金钱、荣耀、地位,每一样,都让人心旌动摇,内外纠缠,不得安宁。人们有些通过满足他人内在欲望而得到外部荣耀,有些又通过外部荣耀来满足内在欲望,不过,最后总是悲伤,越是满足,就越是悲伤。 你想过抽离吗?你是人群的一分子,却又不是人群的一分子,你和他们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却又没有任何感情纠结。你顺着自己满足身体所有欲望,或者不满足,却又无任何痛苦,你只是顺着来,从未想过为什么要这样。 在冬天的小镇上,你租了一套房子,四五点钟的清晨你就起床,看着小镇上的人们,在白雾茫茫中开始起床操持一天生计,他们忙碌,他们吵架,他们赚钱,他们工作,你喝豆浆,你吃早饭,你看报纸,周围的一切,好像都跟你有关系,又好像一切都跟你没关系。你是个陌生的观察者,可又是个熟悉的面孔。你和钱之间的联系是工作,你和他人间的联系是钱,统统没有感情。 抽离是小乘佛教的精髓吗?只顾着自己清净就好。 回到电影。四个独立的故事,我最喜欢的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一个讲的是对外在关系的疏离,一个讲的是对内心欲望的疏离。第二个苏菲玛索的,讲的是得不到救赎的纠缠,第三个婚外情的,讲的是救赎的希望。 这么华丽的电影,每个男人都清丽脱俗,每个女人都身体健美。 只要记得苏菲玛索清晨从大门出来,从爬满蔓藤的小巷子里走到海边那一段,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