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chszy
kchszy
抓斗的花的标记的话,当然可以写一些比较有中国风的一种,然后说出来就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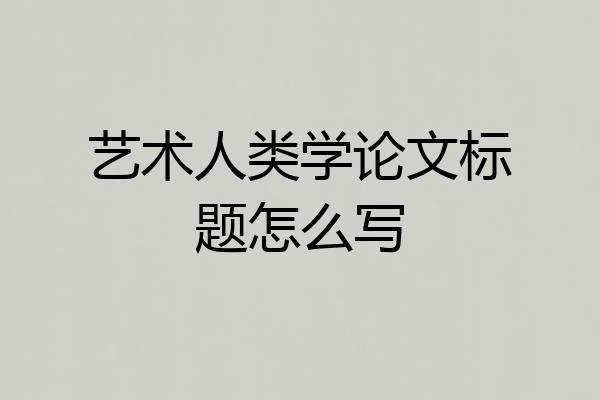
中国传统书画文化的论文小标题应该写什么?那就要看你到底写哪方面的呀?你到底是想写书法呀,还是写会画呀?
求美原则科技论文大标题拟定应着眼简洁、流畅、准确,小标题应着眼简洁、工整、对仗、形似或形近。因此,科技论文标题拟定总原则可以是:立足美,追求完美;追求美,但不苛求美。不必用或重复的语词,坚决不用;可用可不用的语词,最好不用;能不用的语词,尽量不用。具体原则7点。(1)留有余地,求低调。诸如“…研究,…学,…论,…系统,…规律,…机理”字样,要慎用。作者拟题或编辑加工时,在没有彻底了解或掌握文中内容的前提下,不妨低调处理,删除这些“敏感”或“刺眼”的字眼或根据语境用适当词语替换,以体现适当与谦逊之美。(2)删繁就简,求简洁。诸如“关于…的研究,关于…的调查,关于…的探讨,关于…的报告”等字样,作者拟题时尽量规避掉为好。编辑审读加工时,见到类似字样,最好与作者沟通,建议删去这些“多余”字眼,以节省版面,体现简洁性、经济性、可读性之美。(3)便于检索,求特指。拟定标题时,通常提倡用特指性而非泛指性词语。泛指性标题,笼统,概念易模糊,不利于文献检索。倘若根据泛指性标题名所隐含的泛指性关键词在期刊网(或互联网)上检索,那大量甚至海量的类似而相关性不强的文献就会映入眼帘,干扰视线,影响检索效率。特指性标题名,能更好地内涵关键词,既利于文献检索,又便于准确抽取关键词,同时,恰好体现便捷、精当之美。(4)修辞结构,求合理。科技论文标题,习惯用以名词或名词性词组为中心的偏正词组形式表达,尽可能不用动宾结构形式。最好遵从标题用语习惯和简洁性原则,删去赘语。若中心词带状语,则可用动宾结构,比如,“用机械共振法测定引力常数G”。这体现通俗之美。(5)详略得当,求通顺。针对滥用虚词或虚词位置不当或堆砌实词或漏掉实词等现象,在不违背语法修辞的前提下,如果标题名不用某词(字)也通顺,就尽量不用;如果舍去某词(字)便不通顺,就留用之。比如,“沈阳市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去掉“的”字也通顺,但最好规避“研究”字样,用“分析”等字样替代之,即改为“沈阳市水资源承载力分析”更得当。这体现通达之美。(6)结构相同(或相似),求工整。这是针对小标题(层次标题)而言。同一层次标题应尽可能用“排比”修辞手法,即词组(一般词组)结构相同(或相近),意义相关,语气一致。也就是说,所使用的词组应是同类或大致同类,比如说,都是名词性词组或主谓词组或动宾词组等;但要避免“过编辑现象”,即为了求“排比”形式美而不顾科学性和技术性需要,苛求凑字数求工整。一般来讲,编辑加工时,要注意同作者沟通、商榷,要时刻注意科学性与形式美的有机统一。这体现韵律之美。(7)干净明晰,非重复。针对机械重复上级标题字面内容的现象,作者拟定各级小标题和编辑审读加工时,应遵从简洁原则,去掉重复内容。作者不要“惜字如金”,编辑也不要“姑息迁就”,而应以干净文章版面、增强结构美感、打造期刊形象、传播美好文字为出版理念。这体现清洁之美。
理,或者叫做想象。”[1]P163“理性范本”地塑造是个推理、想象出的虚构性的形象,但这种形象却符合范本内在联系的逻辑性。“那位有充分自制力的人全凭揣摩工夫和判断力演戏,他表演的将是日常经验中看到的那个样子,比那个一半凭自然,一半靠揣摩,一半根据一个范本,另一半依照另一个范本表演的人更具统一性。”[1]P326狄德罗所欣赏的戏剧表演家克莱蓉就是这样:她在表演之前就“已塑造出一个范本”,并“设法遵循这个范本”。“她在塑造这个范本的时候要求它尽可能的崇高、伟大、完美。”[1]P282 3.不动感情的表演。演员心中确定了“理想的范本”之后如何表演呢?狄德罗认为“凭感情去表演的演员总是好坏无常。你不能指望从他们的表演里看到什么一致性;他们的表演忽冷忽热,忽而平庸,忽而卓越,今天演得好的地方明天再演就会失败,昨天失败的地方今天再演却又很成功。但是另一种演员却不如此,他表演时凭思索,凭对人性的钻研,凭经常模仿一种理想的范本,凭想象和记忆。他总是始终如一,每次表演用同一个方式,都同样完美。”[1]P281-282 显然狄德罗并不欣赏演员易动感情的表演。狄德罗认为“理想的范本”确立以后,演员将其作为范本固定下来,在演出过程中将已经塑造出的这个理想化、理性化的范本准确、逼真地扮演出来,主要是毫厘不爽地显现出情感和性格的外在标志,这就要求演员不动感情、冷静理智的扮演。“因此最伟大的演员就是最熟悉这些外在标志,并且根据塑造得最好的理想范本最完善地把这些外在标志扮演出来的演员。”[1]P341狄德罗认为演员应该将自己作为旁观者那样冷眼观看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并判断自己的表演正确与否。他说“我要求伟大的演员有很高的判断力,对我来说他必须是一个冷静的、安定的旁观者,因此我要求他有洞察力,不动感情,掌握模仿一切的艺术,或者换个说法,表演各种性格和各种角色莫不应付裕如。”[1]P280-281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演什么象什么”,如克莱蓉就会不动感情地复演自己所塑造的形象:“象我们有时在梦中所遇见的一样,她的头高耸入云端,她的双手准备伸出去探索南北极。她象是套在一个巨大的服装模特儿里依附到自己身上。她随意躺在一张长椅上,双手叉在胸前,双目紧闭,凝然不动,在回想她的梦境的同时,她在听着自己,看着自己,判断自己,判断她在观众中产生的印象。在这个时候,她是双重人格;她是娇小的克莱蓉,也是伟大的亚格里庇娜。”[1]P283 狄德罗认为演员的才能就在于他们并不象观众所想象的那样易动感情,演员的表演是摹仿出记忆中已经设想好、塑造好的动作和表情。他们的表演尽管虚假却生动逼真:一个男演员和他的妻子是冤家对头却在舞台上扮演一对温柔多情的情侣,他们所说的台词与他们心中所想的完全是两回事;一位女演员欺骗一位骑士的感情却对已知真相、前来看戏的骑士嫣然一笑,丝毫不受骑士的突然出现而影响情绪,继续扮演戏中感人肺腑、引人痛哭流涕的角色;一位女演员在表演时嘲笑被她的表演感动的老人。狄德罗特别欣赏演员嘉理克的表演,因为他在短时间内非常逼真地摹仿出许多表情模式。“嘉理克从两扇门扉之间探出脑袋,不到五秒钟的工夫,他的脸部表情先是大喜欲狂,然后是有节制的喜悦,然后是平静,再从平静到惊奇,从惊奇到大惊,从大惊到忧郁,从忧郁到沮丧,从沮丧到惧怕,从惧怕到恐怖,从恐怖到绝望,最后从绝望又回到开始时候的表情。”[1]P301 短时间内能摹仿这么多表情显然是演员恰如其分地控制了他表演的每一个表情。 三、狄德罗戏剧表演理论的评析 对于演员如何表演历来是个争论的问题,《演员奇谈》里面也提及到许多人物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据近代文艺心理学的研究,演员们确实可以可以分为两派:“分享派”(分享剧中人物的内心生活)和“旁观者”(旁观自己的表演);这两派的代表之中在表演艺术上都有登峰造极的。”[2]P271 这个问题的见解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在西方古典主义时期伟大人物是舞台主角时,就需要冷静理智地扮演出伟大人物的崇高形象;而近现代平民主体地位普遍上升,要还原人类真正的天性,就需要更多地体验人类这种天性和情感。狄德罗并没有完全摆脱古典主义的影响,他仍认为舞台所塑造的形象应该是典型化和理想化的形象。启蒙思想的理性主义又让他认为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应该不同于日常生活那样任由情感驱使,演员要严格控制自己的感情,保持清醒和理智的头脑,使得自己的表演逼真地摹仿出所塑造的“理想的范式”。他认为逼真摹仿自然的戏剧自然会产生强烈的审美效果。《演员奇谈》中谈到当时那不靳斯王国的一位戏剧诗人对演员进行六个月的艰苦训练,最终“每人都与自己的角色融为一体”。这里的训练即对角色的塑造是靠推理和设想,而不是靠情感体验。他们连续演出六个月,“国王和他的臣民享受到戏剧幻象能给予人的最大乐趣。这个幻象在第一次演出和最后一次演出时同样强烈。”[1]P332演员每次不动感情、逼真的摹仿对观众那么具有吸引力,这也说明不动感情的表演还是有其生命力和合理性的。事实上确实有些不动感情进行表演而获得极大成就的演员,也有与狄德罗持相同观点的剧作家,如莎士比亚就劝告演员表演要节制和镇静,不能凭一时的心血来潮。[2]P270-271 狄德罗作为剧作家的身份决定着他缺乏戏剧表演的亲身经历和体会,所以他的戏剧表演理论过于偏激。他的理性主义有些机械成份,过分强调认识的高级阶段——理性,而对形成理性认识初级阶段的感性认识认识不够。另外人类的认识是在实践中形成和丰富的,而实践是个主客观互动的过程。戏剧表演是要给观众观赏的,观众的观赏效果对舞台表演有着很强的互动性,舞台的现场效果往往可以影响演员表演的张力。狄德罗对感性认识的模糊也影响他对人自身的心灵与身体一体的天性缺乏认识,也就不能认识到演员在扮演角色的过程中会回归到角色自然本身的天性上来,所以他并不认为有体验角色本身天性的必要。他要的是被理性化和典型化的人物形象,他要的是表演对自然逼真地摹仿以及对观众的认识和教育作用。狄德罗没有辨证地看到体验和摹仿之间的关系,而过分拔高逼真摹仿的一面而忽视体验在戏剧中的重要性。其实在塑造“理想的范本”之时演员对典型形象的塑造并不主要靠设想,而应该主要靠情感体验,通过情感体验去把握典型人物的形象塑造。在演出阶段应该也有情感体验的因素,当然这个情感是理智控制的情感,情感失控是会影响表演的,而缺少情感也不能激发演员达到最佳的表演状态和激起观众的情绪反应。 在演员方面狄德罗认为“极易动感情的是平庸的演员;不怎么动感情的是为数众多的坏演员;唯有绝对不动感情,才能造就伟大的演员。”[1]P287他认为如浪子和烟花女子之类的人最适合当演员,“一天到晚快快乐乐的人既没有大的缺点,也没有大的美德;一般说以插科打诨为业的人都秉性轻浮,并没有坚定的原则;那些与社会上某些窜来窜去的人相似,没有任何性格的人,偏偏擅长表演所有的性格。”[1]P319浪子和烟花女子之类的人能够揣摩和塑造出各种角色的性格,能够成为优秀的演员并非他们这些人本身没有坚定的性格,也并非在于他们表演时能够做到绝对不动感情,而是因为浪子和烟花女子他们生活经历曲折和丰富,他们对生活、对社会有着深刻地体验和认识,他们的表演才会入木三分,所以演员的表演也并非与他们生活的体验完全没有关系。 注释: 1、《狄德罗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4年版。 2、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7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