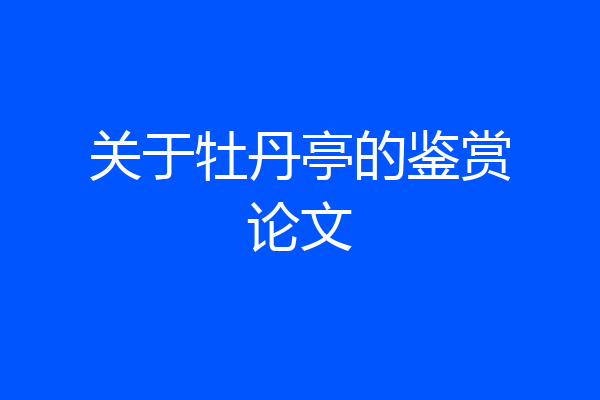小郝a学习
小郝a学习
(1)杜丽娘是无情世界中的有情形象。她的爱情是发生在不允许其生长的环境之中,她的父母和他的教室都是封建道德去束缚她管教她。杜丽娘的性格与这样的环境形成矛盾冲突。(2)性格发展的三个阶段:1、游园惊梦。是对传统道德礼教的大胆挑战,是她反抗性格的关键。第一次走出了深闺书房,第一次接触大自然,春意盎然之景,由此引发其感慨青春不再。2、迅猛陡然。使她为情而死,然而又一往情深。阎王见其在冥间也执着追寻爱情,使他回生,终于与柳梦梅相结合。这是其反抗叛逆性格的升华。3、历经劫难的爱情却遭到其父的反对,杜丽娘挺身捍卫,反抗性格的成熟。(3)她在反抗道路上的每一个行动都是晃动了沉重的精神镣铐,充满了内心矛盾,杜丽娘是封建礼教叛逆者的典型。 纯手打,望采纳,谢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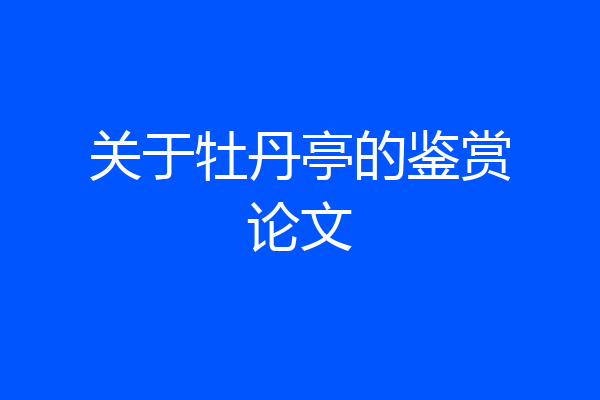
一 汤显祖的《牡丹亭》“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奇气郁勃,博辩纵横”,其中的独特人生感受是常人难以体会的。他自己说:“玉茗堂开春翠屏,新词传唱《牡丹亭》。伤心拍遍无人会,自掐檀痕教小伶”。时人也说,“由于作者早岁以诗文鸣于时,又是一位属于泰州学派的思想家,喜欢议论时政,所以人们对待他的剧作往往不肯‘就戏论戏’,总认为戏剧形象中藏着许多机锋,寻味不尽”(《昆剧演出史稿》陆萼庭着赵景深校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59页)。怎样认识昆剧《牡丹亭》的文化意义?我想,首先是要看戏、看剧本,但是读一下英文译本,看看外国人的说法,也许会有所启发。再说,因为人类学的描述方法是接近于文学的,因此人类学家就可以象文学批评家一样,“解读”剧本。“人类学者的工作就是选择一项引起他注意的文化事业,然后以详尽的描述去充实它并赋于说明性,以便告诉他的读者理解他所描述的文化的意义”(《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马尔库斯费彻尔着三联书店1998年52页)。 莎翁和汤显祖属于同一时代,两人都是1616年逝世的。《牡丹亭》的译者白也(CyrilBirch)说,汤显祖的“题词”写于1598年,和地球另一面莎士比亚写《罗蜜欧与朱丽叶》近于同时。更为相似的是汤显祖的《牡丹亭》应了西人的一句谚语,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这两位大戏剧家不仅活在同一历史时期,而且思想也是相通的。至今,不仅中国人说不尽,外国人也说不尽。“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Without visiting this garden,how could Iever have realized this splend or of spring!)这也可以是一种暗隐:不能理解古典昆剧艺术,是没有文化的表现。美国波士顿Cheng&Tsui出版公司自称“骄傲”地出版了全本55出的《牡丹亭》(英文ThePeonyPavilion或拼音MudanTing),并且被评为美国1981年的杰出学术著作。译者用的是徐朔方、杨笑梅的《牡丹亭》校注本。书封面的介绍写得简明扼要,“产生于16世纪晚期的明王朝的这本古典戏剧故事,说的是杜丽娘梦到了一个理想的爱人;但没有希望再遇到他,于是不平静地死去。她好象死了,如鬼一样不断地寻找她的梦中的爱人,直到这个爱人最后发现了她自画象;这个爱人也梦到了她,爱使她神奇地活了过来”。 译者的“前言”首先引用了汤显祖的“题词”:“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漠中求得其所梦者者而生”。汤显祖知道这种“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世人是不相信的,“形骸之论也”。所以他辩解说,故事是有本源的,而且“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这是强词夺理,但因为我们读了书,看了昆剧《牡丹亭》后,深深地感动而原谅他了。在汤显祖来说,“情”是伟大的,它来自内心,不可抑制,是对冷冰冰的封建理性的胜利。 的确,汤氏的官场情尽,借《牡丹亭》的男女之情表现个性解放之情,自由之情,“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杜丽娘不仅是少女的怀春,而且暗喻着个性解放的自由思想:“至情”可以“还魂”。“作家感到人民的痛苦,青年的受压,以及知识分子的才能无所用,这种时代和社会的苦闷和渴望出路的希冀凝聚有作家的笔端,折射在杜丽娘的性格之中”(《昆剧艺术》创刊号64页)。明人王思任说,“情不可以论死,死不足以尽情,百千情事,一死而止,则情莫深于阿丽者矣”。嵇康在《释私论》中说,“越名教而任自然”,人的自然本性与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游园》、《寻梦》二场,集中地表达了崇尚自然的思想,“可知我一生儿爱好是自然”是画龙点睛之句。古人寄情于戏剧,以美女来寄托自已的政治理想,这是自屈原《离骚》以来的传统,“美人香草,皆忠臣孝子之寓言”。这需要不断地领悟和反思。连伟大的毛泽东都说,读了几次《离骚》,又有新的体会。吴梅说,《牡丹亭》“在生死之际”,前五折“由生之而死”,后五折“自死而之生”(《吴梅戏曲论文集》王卫民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156页)。杜丽娘死了再生,确实是此戏的中心,是作者希望的理想不灭。封建主义可以死灰复燃,民主主义为什么不能如杜丽娘一样“月落重生灯再红”呢? 译者又说,在汤显祖时代,南戏到达了它普及的高峰。它的特点是青年男女之恋,遇到阻力,但最后是大团圆。杜丽娘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值得崇拜的女英雄之一。戏有一种闲散的优雅的味道。在优美的气氛中,用诗一样的语言,分析了戏中生死间主要的各种角色,作出了“深刻的哲学论断”。又说,在充满阳光的星期天的草地上,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大学生读此书,也可以做一个好梦。而且,青春少女杜丽娘,有着一般性的特点。潘光旦老先生说,“寻常在结婚以前守身如玉的青年容易做白日梦”。他以古书为证:“有二八佳人,端立于上,艳丽无匹,徐乃作回风之舞,如履平地,婉转袅娜,百媚横生,两袖惹云,不粘不脱”(性心理学霭理士原著潘光旦译注生活读书新知出版社1988年172页)又有宋代一女,年十七卒,“每当疏雨垂帘,落英飘砌,对镜自语,泣下沾襟。疾且笃,强索笔自簪花小影,旋视良久,一恸而绝”(同上179页)。明代杭州有女伶名商小玲,以色艺称,善演汤显祖《牡丹亭·还魂记》,后因片面相思,郁郁成病,终死在红氍毹上。这些古书上的描写,和杜丽娘何其相似乃尔。李渔的朋友苏州人尤侗作《钧天乐》。此剧嘻笑怒骂,攻击科场黑暗。又与《牡丹亭》相通,主人翁“为情而死,死可以复生”。近代何其芳《画梦录》中也写过一个农家十六岁小女的早夭。“现在我梦里是一片荒林,木叶尽脱。或是在巫峡旅途间,暗色的天,暗色的水,不知往何处去。醒来,一城暮色恰像我梦里的天地”(《画梦人生》何其芳美文何乃光编花城出版社1992年1页)。 二 译者的另一本精心之作是《中国人的舞台-明代精英戏剧》(《SCENESFORMANDARINSTheEliteTheateroftheMing》CyrilBirch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一书。它的主题是介绍明朝精英和舞台的关系。他曾在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学习和教授中文。这个学院,我是去过的,里面的中文图书馆据说是英国之最,里面的外国留学生特别多,黑人很多,墙上还挂了大幅的中国传统山水画,只是我在学院的食堂里吃过的一顿洋饭倒不敢恭维了。 只是无巧不成书,白也教授此书开头有一段与我的一次看戏的现场觉特别相似。这位美国老专家说,昆剧产生于17世纪转折期,这是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设想“四百年前,一些外国人访问了大运河边的苏州古城”,“其中一些人被邀请参加中国人私人住宅的社交活动”;“今天是我们的朋友江苏省总督的生日,我们和一个小群体一起庆贺。总督的衙门比通常安静”,“在宽敞的住宅里有大型的活动”。他还说,这是一个春天的日子,牡丹花也开了,竹林里的路也扫干净了;厨房里准备了太湖的鱼;在新建的大厅里有些冷;看戏的厅堂十分高大,装饰精美。最主要的是有戏,家班和乐队已经在台侧等候了,点的戏是“轻松的喜剧,对话充满智能,唱腔如诗如画”。白也老先生介绍的背景和我们今天看戏的背景何其相似,博物馆古戏台就是在昔日的总督(实际上是巡抚)府内,后面是拙政园。 台上王芳扮演的杜丽娘正唱着: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 便赏心乐事谁家院 台上基本上是一人一桌一椅一灯。但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演出中,却把观众带进了艺术境界之中。这折由“传”字辈和张继青老师等教的《牡丹亭》,“幽深艳异之致,为古今诸曲所不能到”,可以说是我国传统戏曲中艺术表现手法的典范。如果演员缺乏足够的功力,是决不能胜任演出的。台下,观众沉浸于昆曲的美之中,唯恐曲终人去。昆曲是最能表现中国传统抒情的一种艺术,它把歌、舞、诗、戏合成那样精致的一种形式。西方一些歌剧似是有歌无舞,一味地唱,遗憾的是近来炒得很红的京剧《中国贵妃》倒有些象外国歌剧了。昆曲却能以最简单朴素的舞台,表现出最优美的情感。在现代全球商业文化一统天下的情况下,苏州还是有这样传统文化的精品,实在是苏州人的骄傲。现在要继续保持这个地位,就得一代一代传下去。 案头本子再好,剧本再缩编,如果没有舞台的发挥,影响是不会这样大的。传统的几百年留下的演出手法,是世世代代的老一辈演员传下来的,是非常珍贵的。的确,不少传统折子戏经过数百年来的创造性劳动,演员的不断加工处理,演员的表演经验使之显得更加光彩动人。如苏州清代集秀班是“苏班之最著者,其人皆梨园父老,不事艳冶,而声律之细,体状之工,令人神移目往,如同古会。非第一流不能入此”。清代金德辉擅演闺门旦(昆班叫五旦),《寻梦》是其代表性演出。他的演出,“冷淡处别饶一种哀艳”。令人想起古人的诗:“氍毹祗隔纱屏绿,茗炉相对人如玉”,“当筵唤起老临川,玉茗堂中夜深魄”(《鸳湖主人出家姬演〈牡丹亭〉歌》,《明诗纪事》辛卷二十二)。这是多么动人呵! 苏州昆剧《牡丹亭》是到文革以后,重振旗鼓的。这时人们才重新承认了昆剧的崇高地位。这是当时张继青演出的意义。长期以来,昆剧没有这样的地位了。张继青的这段歌舞:“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十分精彩,据说是超过“传”字辈,也超过梅兰芳(仅就此而言:在59年代的记录片上,作为老年男性的梅再演花旦,自然是不及青年女子美丽了)。张继青中年时表演也不凡。虽然,台下是一个普通的妇女样,但台上可以表现出一个年轻的小姑娘,仍“喉若雏莺静女”。正如古人所说,“清柔而婉折,一字之长,延至数息”,运气自如。她并以宁静的舞姿表现忧郁的心情,有时略开笑颜,摇扇舞袖,与飞燕啼莺共游园。传统的《牡丹亭》就是这样朴质无华,“本色清言、寻常茶饭、绝俗离世”。 在忠王府古戏台的演出方式,一如旧制,包括出将入相、检场等,灯光也用的是大白光,突出的是演员的表演。朱家溍老人尤其欣赏这出戏的伴奏方式,仅用南弦(即三弦)和月琴。他说:“何必非要加大提琴、大贝司呢?昆曲,就是要听她清雅的风味,配乐如果搞得太浓艳,有时会破坏古典的韵致和意境”;“并不是外国有的乐器,都可以搬进昆剧里来的,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前辈早就注意到了。那么多的中外乐器,为什么都没‘引进’昆曲呢”?朱先生强调说:“古人不是傻子。他们知道昆曲应以怎样的风貌示人。其实,昆曲的配乐经过好几代人的磨洗,已经找到了和谐的结合方式,如一般用两根笛子和三弦、月琴,生旦戏加笙,净丑戏加唢呐等”。 外国人也来“游园”了,现在有不同版本的全本《牡丹亭》演出,这是全世界的热潮。一是由美国华裔导演陈士争执导的全本55出《牡丹亭》,我在网上,看到了陈士争执导的全本55出《牡丹亭》广告。后来,还看到了全本的录象。另一是上海昆剧团自排的《牡丹亭》。香港学者古兆申,也有意新编《牡丹亭》。他说,我的原则只有两条:第一、改编本必须充分发挥原著的题旨;第二,必须保留昆剧舞台艺术的优点和特色。我想,再下去,也许要有一种新的改编,可参考西方大片英国《莎翁情史》,将莎士比亚的事迹与《罗蜜欧和朱丽叶》的情节穿插在一起,但这种创作方法在清代蒋士铨的《临川梦》一剧中早有表现,汤显祖和杜丽娘都在舞台上出现。苏州仍需要一个比较全的本子。顾笃璜整理过《牡丹亭》一个本子,已经试演过。现在还有他人,加工演出。剧本缩编是一项本事。苏州作为发源地,在坚持传统特色上应当做得更好些。
论青春版《牡丹亭》现象 -------------------------------------------------------------------------------- 【作者】朱栋霖 【内容提要】青春版《牡丹亭》提炼了汤显祖传奇的青春与爱情主题,以典雅柔美的昆曲艺术演绎了一段生死恋情,在当代大学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引领了一条中国昆曲遗产保护传承、薪火传续、代有传人的路子。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展示了中国昆曲正宗的艺术与美学风貌,赋予古典艺术遗产以青春的生命,也为青年学子提供了与传统、古典对话的空间。 2004年4月由白先勇策划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在台北首演,9000张戏票早就抢购一空,《联合报》破例头版头条刊登首演消息。青春版《牡丹亭》上演成为当年台湾一个轰动的文化事件。2004年5月青春版《牡丹亭》轰动香港剧坛。2004年6月,苏州大学存菊堂内2400个座位满满当当,开演前已是一票难求。11月,在上海国际艺术节上青春版《牡丹亭》依然红火。2005年3月青春版《牡丹亭》成为澳门国际艺术节上最具看头的剧目。2005年4月8日起,青春版《牡丹亭》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演出。每到一处,校园里就掀起一阵热潮,剧场内掌声迭起,大学生好评如潮,称观看青春版《牡丹亭》是一次心灵的震撼。2006年4月,青春版《牡丹亭》二度进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演出,依然盛况如前。 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已是近年来中国戏剧界影响最大、最引人关注的事件,尤其是她走进高校,在中国大学生中产生的轰动与影响,使这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可称之为“青春版《牡丹亭》现象”。 一 形成“青春版《牡丹亭》现象”的主要原因,我提炼出三个关键词:“白先勇”、“青春版”、“中国昆曲”。 一、“昆曲义工”白先勇。白先勇先生以其智慧决策、美学导向与组织才能,在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策划与演出中所起的核心与决定性作用,已是有口皆碑。他杰出的文学创作成就以及他本人在文化界、高校中的巨大影响,是本次拓展青春版《牡丹亭》在台港澳、在中国大陆的影响与成功走进高校的最大推动力,这也是无可置疑的。可以说,他是青春版《牡丹亭》演出的灵魂。三年来,他搁置写作,基本坐镇苏州,在台北与苏州之间往来奔波,对剧本整编、排演的大小环节悉心指导;每次演出之前,又马不停蹄,亲自出马宣传造势,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受记者采访、到各大学演讲、与大学生座谈。演出之后又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不断推敲、修改演出。他的“昆曲义工”精神感动了大家,台北的艺术家、大陆、香港的教授专家与研究生、大学生们,都愿意为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奔忙。 二、诉诸至情的“青春版”。白先勇先生拈出“青春版”三字作为这次昆曲《牡丹亭》搬演的题旨,我认为这是其成功的关键。 它强调与提炼了汤显祖创作的“青春与爱情”主题。《牡丹亭》问世以来的演出,各个时代曾有各种各样的理解、诠释与处理,如“艳情”、“鬼情”,而近50年来的流行看法是“反封建”,因为柳、杜“反封建礼教”,《牡丹亭》才得以继续公演。在一段时期,《牡丹亭》也可以被诠释成歌颂杜丽娘追求个性解放。而白先勇则从《牡丹亭》中四百年前的唯美绮梦,提炼出一段缠绵古今的生死恋情,杜丽娘为情而死、因情而生,死死生生中唯情是灵魂,汤显祖以“情至”为自己创作追求的精髓。强调青春与爱情的主题,更符合汤氏精神,也贴近白先勇策划《牡丹亭》锁定的观众群——当代青年人的心灵。 青春版《牡丹亭》对“青春与爱情”主题的提炼,乃是真情、纯情、痴情、至情,是刻骨铭心、生死不渝乃至跨越生死之情。《牡丹亭》表现的至真恋情,已为今日文艺作品所鄙弃,今日铺天盖地描写爱情婚姻的作品大都表现三角恋、婚外恋、乱伦恋、非道德恋、变态恋、移情别恋,包括流行歌曲、影视剧。在那些作品中,爱与情总是与非道德、与乱、与恶、与邪相维系,描写真情、纯情、至情被嘲笑为陈旧、保守,不合时宜。因此当《牡丹亭》剧场中浓郁的真情、纯情、至情被激荡起来,一下子唤醒了人类心灵深处饥渴的真纯之情,尤其是剧场中年轻的心。剧中缠绵四百年的爱情梦想是中国人心底的爱的情结,是人类心灵的渴望。正如白先勇所说,虽然现代人比较浮躁,但是内心总有一个自己的爱情神话,现实中可能得不到、太难得,而《牡丹亭》中爱情的真挚以及表演的优雅,使此剧得以超越时代,令其获得年轻人的欣赏成为可能。每次演出,都激起青年观众如潮掌声与心灵震撼,说明它对e世代青年具有吸引力,青年大学生是今日社会上纯情一族。这是一个爱情神话,一对痴情的情人舞动翩翩水袖唱着纯真优雅的情歌,将青年人的心灵之窗打开。 青春版《牡丹亭》的剧本整编,颇费经营。他们考虑到,对于不熟悉古典戏曲情节的青年观众,片断式的经典折子戏无法使他们产生理解与共鸣,需要演全本。戏剧的意义,是在剧场中通过“演”与“观”的互动产生的。连续性的情节才能产生情感的激动与心灵的投入。以“梦中情”、“人鬼情”、“人间情”提纲挈领形成上、中、下三本;为了体现汤氏原著精神和艺术风貌,对原作遵循“只删不改”原则,将原作55折提炼、整编为27折,保留了全部经典折子戏;加强了柳梦梅的戏分,使杜丽娘、柳梦梅的戏成为剧中两条互相呼应起伏的戏剧行动主线,形成耐人寻味的戏剧复调来丰富戏剧内涵。又以杜宝奉旨抗贼、强盗李全杨婆夫妇的活动为副线,形成全剧文武场、冷热场交叉协调,使全剧充满剧场张力。 青春版《牡丹亭》启用青年演员来饰演处于青春爱情中的男女主人公,是这次演出获得轰动效应的根本原因。就象当年好莱坞影片《泰坦尼克号》全球轰动一样,因为男女主人公青春靓丽,是影坛新人。 戏曲舞台演出的特点是演员的“肉身化”的表演,戏剧的文学、音乐、唱腔、舞蹈、做功、舞美、服饰到导演构思与舞台调度、对人物的理解与处理,以及昆曲艺术的诗化意境等,这一切都要通过演员的肉身化表演来实现。演员的“肉身化”形象——“扮相”十分重要。因此,戏曲表演要求色艺双全,乃是戏剧观赏的情理与美学规律所致。 白先勇以其艺术敏感,选定苏州昆剧院“小兰花”班青年演员沈丰英、俞玖林出演《牡丹亭》的“梦中情人”。他们与剧中人杜丽娘、柳梦梅的年龄相仿,正值青春年华。沈丰英、俞玖林以清俊优雅的舞台形象与自然细腻的表演,赋予汤显祖的古典形象以活泼新鲜的血肉。舞台上的演员就是有血有肉、有真情真爱的真的杜丽娘、柳梦梅,这对情侣不只用缠绵的水袖来表达缱绻的恋情,而且眉目传情,举手投足温情脉脉,成了青年观众的梦中情人。我们在好几所大学的观众中了解,有的同学是看了海报的靓丽剧照去看戏的,不少女同学是喜爱男女演员的俊雅靓丽才第一次进剧场看了昆曲。 三 、古典美学精髓——中国昆曲。中国昆曲终于有机会面对当代大学生嫣然一展其宁静、优雅的古典美,汤显祖的杰出才华在《牡丹亭》演出中得以淋漓尽致挥洒自如。这让二十年来处于流行歌曲摇滚乐、西方文化肯德基包围中的当代年轻人,真正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青春版《牡丹亭》剧场中,真正让当代青年心灵震撼的,真正使大学生被征服的,是中国昆曲自身的艺术魅力。昆山腔经魏良辅改革,成为一种格律严谨、声腔音乐婉转悦耳柔媚悠长的演唱艺术。又浸润过许多文学艺术家的智慧,昆曲艺术成为融汇文学、戏剧、表演、音乐、舞蹈、美术于一体,富有诗情画意的舞台综合艺术,它集中国古典艺术与美学之大成,独具神韵的中国戏剧诗风格,具有永远的魅力。而汤显祖的文采词章、横溢才华,他对戏剧情节、戏剧人物的新鲜别致、想落天外又游刃有余的独特描写,使青年观众惊喜赞叹连连。这是一出中国文化的盛宴,是中国古典美学的胜利。 二 将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称之为“青春版《牡丹亭》现象”,是鉴于其演出的意义已超越了一出戏。我认为,它是继上世纪50年代昆曲《十五贯》之后,在中国昆曲的弘扬传承史上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引领了一条昆曲遗产保护传承,薪火传续、代有传人的路子。 中国昆曲虽然在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杰出的文化与艺术价值尽管为世界公认,但是它的濒危的境况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文化的杰出遗产昆曲艺术,能否在21世纪获得保护传承,这是我们面临的文化挑战与世纪命题。 珍爱昆曲如生命的白先勇,看到了昆曲目前面临的危机主要是由于观众老化和演员老化所致,他希望通过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造就一代年轻演员,培养昆曲人才,以青春的演员面对年轻的观众,让传统的经曲焕发出青春的生命。他请来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张继青、汪世瑜,请他们向青年演员亲自传授其艺术真传,并举行了传统的拜师仪式,就像八十年前昆剧传习所所做的那样。昆曲的五百年传承就是靠这样的方式薪火传续、代有传人的。无疑的,从青春版《牡丹亭》的排练到两年来的演出活动中,两位师傅的真传保证了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是正宗、正统、正派的南昆艺术,他们的演唱、表演、风格、他们对剧中人的理解,都在两位传人身上获得了传承。两位师父的倾心传授得到格外的尊重。我注意到从排练到每次演出,“旦角祭酒”、“巾生魁首”的称誉一直如雷贯耳,响遍海峡两岸,白先勇先生每次出席新闻发布会、每次谢幕、每次座谈会,总是都请张、汪两位师傅一起出席。 白先勇力主青春版《牡丹亭》重在推出青年演员。名不见经传的青年演员担纲的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对中国昆曲界在今日需迫切解决的人才培养与艺术传承问题,打破昆剧演员队伍固有的凝固、尴尬局面,具有特别意义。 我国戏曲界的历史与各种原因,造成名演员的年龄已不年轻。戏剧界对此已习以为常。我们欣赏他们的演出,是对艺术经典的鉴赏。对于有经验的戏剧鉴赏者来说,人家都非常熟悉这些经典折子戏的情节,以至于念白唱词行腔都烂熟于心,戏剧的情节内容已在观剧中被淡去,演员的外形扮相对于鉴赏者来说已不重要,戏剧鉴赏的重点在于欣赏与鉴别演员的表演艺术如何以形传神,他的表演与演唱如何达到艺术理想的最佳状态,例如以某个著名演员的表演为标准,以及他是否还能有个人的艺术风格。观剧心理的另一方面是,出于对某一著名演员表演的认同,因而对于他因年龄造成的形体扮相的不足就忽略不计了。上面所说的当然是戏剧鉴赏的理想境界,但这样懂行的戏剧鉴赏者毕竟是少数,在今天只剩下极少数老年观众了。戏剧演出是必须面对大多数观众的,观众进剧场总是通过对戏剧情节与戏剧人物的理解、关注,才能进而欣赏艺术的。某剧团曾安排青年与中老演员分别演《牡丹亭》的上、中、下本,一位青年观众看后说:“他们的唱腔确实炉火纯青,表演已臻化境,但看着他们臃肿的身形,满脸的沧桑却要作出小儿女的种种娇态。我却浑身起了鸡皮疙瘩。”这话虽然使人难以接受,但可能是大多数观众的感受。 戏剧舞台演出的“肉身化”特点,需要青年演员担纲表演主体。现在昆曲界津津乐道当年传字辈顾传、朱传茗的表演。顾、朱的表演,我没亲见,但看当年留下的剧照与剧评,可知青春靓丽是他们当年红透海上昆坛的一个重要原因。顾传当年在上海声誉鹊起时,年仅十五六岁。他二十一岁时被梅兰芳(当年梅兰芳二十六岁)邀请同台演出全本《贩马记》,之后即离开舞台,他的名伶生涯与演艺声誉是在二十一岁之前。另一位名角朱传茗也是在二十岁之前已享誉沪上。剧评与回忆都说,顾传扮相清秀飘逸,举止文雅潇洒,风神奕奕,音调清丽委婉,抑扬自如,表演自然真切,细腻传神,他表演中时有皱眉,更令其表演楚楚动人。朱传铭扮相端庄秀丽,身段优美,表情细腻,唱腔清丽柔润。有人描写顾、朱二位:“正当妙年,或濯濯如春柳,或灿灿如奇葩,清歌妙舞,一回视听,令人作十日思。”(半村主人:《仙霓社之前后》,《红茶》)。当年《申报》是这样评论仙霓社传字辈的演出的:“今日新乐府之脚色,皆为年青子弟,扮相甚佳,行头亦颇漂亮。所演之剧,均能破除沉闷,以迎合社会之心理。”(1928年)想当年梅兰芳在北京初登菊坛崭露头角,尚在十八九岁,他的风头甚至压倒“伶界大王”谭鑫培,主要还是得之于青春的优势与表演细腻,吻合大众的观剧审美心理。1923年程砚秋邀俞振飞在上海丹桂第一台演出《游园惊梦》,珠联璧合,佳评如潮,那一年程二十岁,俞二十二岁。他们当年的演技决不可能已达到后来的大师级水平。 昆曲艺术是以生旦戏为主的,剧目的这一特点与昆曲成长于江南、也成熟于江南文化这一特点相融合,昆曲艺术是充分体现了“江南春色”的美学特色的。它尤其需要演员的年轻化,清俊文雅的生旦无疑也是昆曲舞台表演艺术的美的追求。设若没有了生旦的清俊优雅,昆曲的典雅柔媚婉转的艺术风格就会损失不少,演员形体的变异与生旦角色美的要求之间的错位造成的遗憾,是很难弥补的。不管这舞台是如今镜框式舞台还是古典厅堂的红氍毹演出,后者由于观、演距离的贴近更要求优伶年轻可爱。所以昆曲史上,无论是明清家班还是清代职业昆班,都挑选青少年为戏班优伶。如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自述其家班:“自大父于万历年间与范长白、邹愚公、黄贞父、包涵所诸先生讲究此道,遂破天荒为之。……主人解事日精一日,而童技艺亦愈出愈奇。余历年半百,小自小而老、老而复小、小而复老者,凡五易之。”(《陶庵梦忆》卷四“张氏声伎”条)张氏不惜花费重金,五易其人,以保持家班演员的年轻化。 三 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展示了中国昆曲的正宗的艺术与美学风貌,赋予古典昆曲遗产以青春的生命。这是中国美学的胜利。这在今日全球化、现代化的浪潮中,尤其具有意义。近二十多年来,戏剧行业全面衰落,观众大量流失,曲高和寡的昆曲尤甚。青春版《牡丹亭》在苏州大学首演,我最初的估计是需组织四百观众在小礼堂演出,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能够耐心观看昆曲的大学生只有几百人,而且还难以保持三场不走人。但是白先勇先生专门从台北打来电话,希望进入二千多座位的大礼堂。结果连演三天,无需组织观众,七千多人次全部满座,盛况空前。大学生赞叹:“唱腔婉转悠扬,唱词高雅清秀”,“舞台简洁独特,意境美妙无比”,“昆剧真的是国粹!” 这是中国戏曲的一个奇迹!奇迹的产生,我认为当然离不开白先勇先生个人的魅力与努力,不应低估两位年轻演员的成功扮演与全体的努力,但是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昆曲自身的魅力,是中国美学的胜利。 白先勇说:“昆曲是唯美艺术,追求美是我的出发点和归宿,我就是要叫中国的古典美还魂,以美唤醒观众心中的浪漫和憧憬。” 大家都在试图说明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以期求得中国古典戏曲复活的可能性。 北京世纪剧院演出归来,苏昆院长蔡少华告诉记者,北京的评论认为古老艺术与现代审美的完美结合也是青春版《牡丹亭》成功的重要原因,毕竟面对的是21世纪的观众,他们的审美标准已经随时代有转变,青春版《牡丹亭》抓住了这种转变。“采用了全新的手法来演绎他们的爱情神话。”这是一种很流行的、也很易为潮流所接受的解释。 有的认为青春版《牡丹亭》是因为“改编了”,才“属于我们的”。引用黑格尔的话:“我们自己的民族的过去的事物必须和我们现在的状况、生活和存在密切相关,他们才算是属于我们的。”“如果要把情节生疏的剧本搬上舞台表演,观众就有权利要求把它加以改编,就连最优美的作品在上演时也需要改编。”(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351页)因为社会变化了,人们的心理变化了,戏剧观众的欣赏习惯和欣赏要求也变化了,上演古代剧本时就必须适应这种变化。 我认为,这是对于青春版《牡丹亭》成功的误解,是一种从层层因袭的流行理论中产生的误解。对于保护传承昆曲遗产,是一种误导。 我认为,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与魅力,是中国昆曲自身的艺术魅力。而不是在古典传统之外又加上了现代因素,或者是把古典剧本改编了,改得迎合了现代观众的欣赏习惯与欣赏要求。 这个戏的整编组当然对汤显祖原剧本进行了整编,但他们不称“改编”而称“整编”,他们的原则是“只删不改”,是考虑在上、中、下三本九小时演出单元时间内如何更好地体现汤氏原作的精神,而不是将原剧本改得现代些,以适应今日现代社会观众的新的审美要求。青春版《牡丹亭》中对于爱情与性的相互吸引的刻画,对于剧中人的青春的苦闷、遐想、迷思、浪漫与执著的渲染,那些让今日大学生痴迷和心灵震荡的种种因素,恰恰都是属于原作首创的,而不是迎合今日要求改编的。 剧中的舞美、灯光、服饰、音乐甚至舞蹈与表演,也都有新的创造与设计。但这一切的美学目的是明确的,那就是如何更好地塑造符合汤氏原作的两位男女主人的浪漫爱情与执著痴迷,更好地烘托出汤显祖原作的艺术风格与美学精神。王童为杜丽娘、柳梦梅新设计的服饰,烘托出剧中人的心灵与气质,《惊梦》中花神隐去,一袭白衣的柳梦梅如玉树临风清新俊雅,出现在杜丽娘身边,给浪漫的爱梦增添了清隽的诗意。舞美的设计风格写意简约,吸收了苏州古典园林的艺术要素,那是属于中国戏曲的美学风格,而不是现代话剧的。戏曲音乐家周友良为青春版《牡丹亭》的唱腔全部配乐、配器,全部唱腔都依现存昆曲曲谱,新配的音乐、过场都体现了昆曲音乐特点。周友良音乐设计的一大成功是,他从杜丽娘核心唱段《袅情丝》抽取音乐旋律设计了杜丽娘主题音乐,从柳梦梅核心唱段《山桃红》抽取音乐旋律设计了柳梦梅主题音乐,在杜、柳后来的重要唱段中,在戏剧情节的关键环节,不断地交叉演奏起这两支主题旋律,这是男女主人公的音乐灵魂,是他们的心灵深处的呼唤,也是青春版《牡丹亭》付诸音乐的主题呼唤。它使上、中、下三本九小时的演出在音乐上浑然一体,音乐主题鲜明、印象深刻。 古典戏剧在现代剧场的演出,当然遇到一个古典美学与现代剧场的接轨问题,因为面对的是现代的青年观众。白先勇的态度是:“选择但避免滥用‘现代'”。 负责美术设计的王童说得好:“须抱着谦卑的态度,体味昆曲抽象写意、以简驭繁的美学传统,其实相当符合于现代精神。而昆曲与园林、苏绣三者,同为吴越传统人文、细细体味的代表,也可当作舞台美术、服装设计的援引。让苏州本身的文化,得以溶入青春版《牡丹亭》中,也使我们幕后制作、设计群的共识。”他追求“写意、简约”的美学精神,这正吻合了昆曲的美学精神。 白先勇是唯美的,他的唯美主义的美学原则使他对青春版《牡丹亭》的制作十分讲究,唯求至美精良。“离魂”结尾,黑幕下杜丽娘身披曳地的红色斗篷,手拈一枝梅花蓦然回首,拉起,一束追光留下了杜丽娘对人间无限的依恋。“回生”的结尾呼应了“离魂”,黑幕徐徐拉开,杜丽娘从沉睡中慢慢起来,在晨光中返回人间。这显然是运用了现代话剧的手法创造出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出生入死、因情回生的舞台意境。全场的掌声就是对于这种艺术创造精神的赞许。 青春版《牡丹亭》借助制作中的现代元素,让从未进传统剧场的青年观众领略到中国昆曲的“兰韵幽香”,是中国的古典雅韵。“不到园林,怎知这春色如许!”当正值花样年华的杜丽娘在游园时感叹撩人春色时,很多第一次与昆曲接触的年轻观众也对古老的昆曲发出了同样的赞叹。 我们也不能不赞叹,那是中国昆曲自身的魅力。她的曲词、对白的华彩,她的音乐、唱腔的柔婉,她的表演、舞蹈的袅娜呼应,她的剧中人心灵的丰富激荡,她的舞台的空灵意境,让现代青年观众直接领略了中国文化的风采。 我在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青春版《牡丹亭》的表演艺术是正宗的“苏州风范”,是中国昆曲的正宗艺术,体现了古典昆曲的正统一脉。就是白先勇一再强调的:“正宗”、“正统”、“正派”。 青春版《牡丹亭》两位演员沈丰英、俞玖林的表演,展示了正宗南昆的艺术,让人欣赏到古典昆曲所蕴含的“江南春色”。所谓昆曲的“苏州风范”,是在苏州历代文人雅士的精心指导下产生的。讲究咬字准确、吐字清晰;行腔运音严守家门规范,这些演唱规范来自数百年苏州清工曲家的制谱校订;表演文雅柔美细腻,风骨内蕴,创造出俊雅柔美细腻丰厚、具有书卷气的南方风格。苏州软水温土,风物清嘉,人文灵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江南水文化的滋养浸润是苏州文化审美清俊雅致灵动精细,产生了园艺、丝绸、刺绣、盆景、雕刻、丝竹。而昆曲的歌唱、舞蹈,乃是依循吴语音韵、行腔谱曲,提炼吴中艺术与审美资源而设计、谱写的。“吴音清柔,歌则窈窕洞彻,沉沉绵绵,切于感慕”(明王同祖《昆山续志》)。以吴侬软语唱“水磨调”,恰好表现出苏州文化与审美的需求特点。明清以来许多著名曲家、“拍先”都是苏州人,昆班教习也都聘自苏州(如《红楼梦》中写梨香院)。明清时期各地昆班优伶大都来自苏州,“梨园子弟”曾与“苏州状元”一起被戏称为苏州特产。当代昆坛,从俞振飞到张继青、汪世瑜、蔡正仁、石小梅、吴锦芳、张寄蝶等一大批昆曲梅花奖得主,都是苏州人氏。俞玖林来自昆曲发源地昆山,沈丰英生于太湖之滨,他们都得苏州山水之灵气,他们演唱的曲谱是叶堂旧谱,吐字行腔得自张继青、汪世渝亲授,表演也是张、汪数十年舞台经验的传承,而张继青、汪世瑜又是沈传芷、周传瑛等传字辈的真传。他们的表演呈现的自然是正宗南昆的艺术美与文化意蕴。 四 在今日全球化、现代化的浪潮中,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它显示出昆曲作为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的生命力。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一片骚乱涌动声浪之中,这是中国美学的胜利。 从上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已形成了一种习惯性的、几乎是无可置疑的思维定势与批判态度。那就是,一是批判继承论。虽然不能不承认传统文化有糟粕也有精华,但是凡传统文化一言以蔽之都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与要求,因此必须对此批判地继承;二是传统的现代改造与创新论。传统文化要发挥作用,必须经过现代改造。这种思维定势,在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潮流中愈加强化,思想文化界出于文化改造的迫切要求,对传统文化展开了又一次全面的批判,再加上中国社会的深度政治化,渊源深厚、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传统文化艺术,似乎已被宣判了死刑。几乎一致的看法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与文化,只是为封建社会服务的,它在现代社会不能发挥作用,已经只是一种阻力;若要使传统文化再发挥作用,必须改造它。也是几乎一致的看法是,昆曲内容陈旧,节奏拖沓缓慢,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已是博物馆艺术。 但是在青春版《牡丹亭》剧场中,数千大学生一起为中国古典艺术鼓掌。他们发现了中国古典艺术美的不可抗拒。耐人寻味的是,剧场中的这一代年轻人,在西方肯德基与好莱坞片中成长,在网络游戏、流行音乐、摇滚乐中游走,在后现代快餐文化的熏陶中追逐着通俗、低俗与趣味。传统已被忘却或弃为敝帚。可是,青春版《牡丹亭》给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美的鉴赏,那是一种宁静、典雅、温柔、细腻的古典主义气质,是数百年文人雅士创造的精致文化,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高雅艺术的灵魂。一位大学生说,每次演出开始,唱主题曲“忙处抛人闲处住”,“当领唱头一个‘忙'字一跳出来,所有侵入我国的西洋强势文化,诸如阿依达的歌剧,天鹅湖睡美人的芭蕾,古尔德的巴赫等等统统从空中摔下,跌得粉碎,丝毫不爽。我突然惊觉在剧院里正上演的昆剧就是自己与祖国千年历史的维系点。你看,书本上从小念到的词句都活了,变作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个身段妩媚地温柔地熟悉地向你抛来,你除了一呆一惊之余,便是欣喜若狂。” 青春版《牡丹亭》为青年学子提供了与传统、古典对话的空间。他们从古雅艺术中发现现代美,中国文化的美就是自己追求的美。它既是传统、古典的,又是现代、时尚的。中国古典精神在今天仍有生命力。 当年,《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有人说,青春版《牡丹亭》一出戏普及了一个剧种。一代新的昆曲观众群,从这里开始成长。白先勇最初提出“青春版”创意,这一想法正在开始实现。〔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