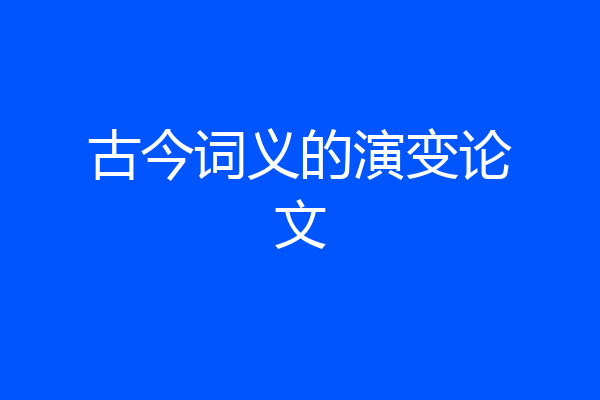liubainian
liubainian
分成本意和四个阶段进行区别即可。 本意(最好是甲骨文意) 上古。(夏商周秦汉) 中古。(魏晋-南北朝) 近古。(唐宋元明清,其中唐又要分别重视) 当代。(主要是简化文字导致的,比如后再古代有2个后,繁体的后与后是2个字,并不通用。)推荐多看一些专业的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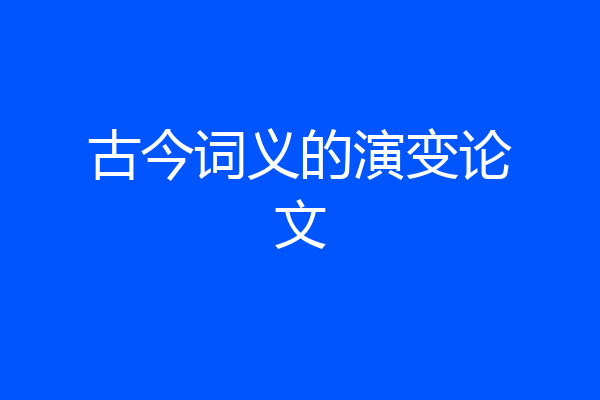
古今词义的演变是异常复杂的,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词义的扩大 词义的扩大是指演变后的词义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范围比原义的范围大。例如:“诗”,古代专指《诗经》,《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现代泛指一般诗歌,词义的范围扩大了。“河”,古代专指黄河。《诗经·魏风·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左传·成公十六年》:“晋师济河。”《庄子·秋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孟子·梁惠王上》:“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河内”指黄河北岸,今河南沁阳一带;“河东”指黄河以东,今山西西南部。汉代以前,“河”的常用义特指黄河。后来泛指一般河流。把一条河的名称扩大成为一般河流名称,由专称变为通称,今义把古义的范围扩大了。“齿”,古义是指排列在唇前的牙。甲骨文画的正是门牙。《墨子·非攻中》:“古者有语,唇亡则齿寒。”后来泛指牙齿。白居易《与元九书书》:“未老而齿发早衰白。”把门牙扩大成为牙齿,“齿”的词义扩大了。“响”,古义是指回声。《玉篇》:“响,应声也。”《水经注·江水》:“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贾谊《过秦论》:“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今义泛指一切物体发出的音响,概念外延扩展了。扩大,就是把意义范围扩大了。第二、词义的缩小词义的缩小是指演变后的词义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范围比原义的范围小。例如:“金”,先秦泛指金属。《左传·僖公十八年》:“郑伯始朝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日:‘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这里记载楚王赏给郑国的“金”,显然指的是“铜”,因为那时铸兵器、铸钟鼎都用铜。楚王担心赏赐给郑国的铜会用来制造武器,所以与郑盟誓。甲骨文中没有“金”字,金文中有了“金”、“铜”,但没有“银”、“铁”,郭沫若认为“铁”出现于春秋时期。到了“铁”、“锡”、“银”都出现以后,“金”就逐渐地专指“黄金”了。如《史记·文帝本纪》:“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金”词义范围逐渐缩小。(现在“五金”、“金工”、“金属”等复合词里的词素还保留古代词义的痕迹。)“宫”,上古泛指房屋。“宫”、“室”是同义词,先秦都指房屋。秦汉以后。“宫”专指封建帝王的住宅,如“阿房宫”、“未央宫”。现在除了某些叫“宫”的旧有名称外,只有某些化娱乐场所才称宫,如少年宫、文化宫。“宫”的词义范围越来越缩小了。“坐”,古代除当“坐下”的动作讲之外,还有“犯罪”、“因为”的意义,《曼子春秋·内篇》“王曰:‘何坐?’曰:‘坐盗。”《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上例的“坐”当“犯罪”讲。汉乐府《陌上桑》:“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杜牧《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上例的“坐”当“因为”讲。现在专指“坐下”讲,今义比古义缩小了。“丈夫”,古代指成年男子。《说文》“周制,八寸为尺,十尺为丈,人长八尺,故曰丈夫。”《韩非子》:“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战国策·赵策》“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后来只指配偶的男性一方,即“妻之夫”而言。概念外延缩小了,就是把意义范围缩小了。第三、词义的转移 是指词义反映的客观对象.由甲类事物转移到相关的乙类事物上去了。例如“坟”,古代本指高大的土堆或河堤。《方言》:“凡土而高且大者谓之坟。”《诗经·周南·汝坟》:“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沿着那汝水的大堤,砍伐那枝条树干)《楚辞·九章》“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大坟”是高大的土堆。远古,人死理起来并不堆土,故《礼记·檀弓》云:“古者墓而不坟。”后来,墓上堆土,就把这种土堆称为“坟”,于是“坟”也就指用土堆起的坟墓了。今义则把原来的“高大的土堆”、“河堤”转移到“坟墓”上来了。“豆”,甲骨文中形似高脚杯,是一种盛肉食的木制的高脚碗。《诗经·大雅·生民》“于豆于登”(盛肉于豆,盛肉于登。”)“豆”就是指这种器皿。后来,“豆”的意义转移到豆类植物及其果实上了。豆类植物,上古不叫“豆”,而叫“菽”。“脚”,原指小腿。中古以后,“脚”指踝骨以下部分,当“足”字解。今义则把原来的“小腿”转移到小腿以下的部位了。“兵”本指兵器。《说文》:“兵,械也。”贾谊《过秦论》:“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成语“短兵相接”之“兵”,都指兵器,今义是指士兵、战士,把“兵器”转移到持兵器的人,就是词义搬了家了,搬到附近的地方去了。第四、词义的褒贬色彩不同 风俗习尚和社会思潮的改变,往往引起人们对事物的爱惜与善恶评价的变化,从而影响词义褒贬的。由于风俗习尚和社会思潮的改变,从而影响词义褒贬的更替。有的词由褒义变为贬义,有的词由贬义变为褒义,有的由中性词变为贬义词。例如:“爪牙”,古代是指武将、猛士,是个褒义词。《国语·越语上》:“夫虽无四方之忧,然谋臣与爪牙之士,不可不养而择也。”《汉书·李广传》:“将军者,国之爪牙也。”“爪牙”的今义是指帮凶、走狗,成为贬义词了。“复辟”古代是指“恢复君位”,是个褒义词,现在是指“反动势力的复活”,成为贬义词了。“锻炼”,古代是指“玩弄法律对人进行诬陷”,是个贬义词,现在指“劳动锻炼”、“思想锻炼”、“锻炼身体”,“锻炼”成为褒义词了。“谤”,古代是指公开指责别人的过失,是个中性词。《国语·周语上》:“厉王虐,国人谤王。”“谤”的今义是指“诽谤”、“毁谤”、“造谣中伤”,成为贬义词了。“贿”,古代有“赠送财物”的意思,是个中性词。《左传·宣公九年》:“孟献子聘于周,王以为有礼,厚贿之。”“贿”的今义是指“贿赂”,即“用财物收买”的意思。成为贬义词了。这样看来,古今词义的异同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古今词义基本相同。有些词的词义没有什么变化,这不仅仅限于基本词汇部分的词。有些词,古今字书的注释大体相同。不仅单音词如此,复音词也不乏其例。早在《诗经》里就有芍药、梧桐、凤凰、仓庚、蟋蟀、苍蝇、参差、窈窕等词,我们阅读古书,按照现代汉语的意义去理解这类词,不会产生什么误解,但这类词在全部词汇系统中只占少数。第二、古今词义完全不同“揭”,古代是“高举”的意思。《诗经·小雅·大东》:“维北有斗,西柄之揭。”(箕星之北有南斗星,西翘长柄,向东远伸。)《战国策·齐策》:“于是乘其车,揭其剑。”后以“昭然若揭”形容真相毕露、明白清楚。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成语词典》把“昭然若揭”释为“明显得像揭开盖子一样”.这是不了解古今词义的差异而造成的误解。现代“揭”的常用意义是指把盖合或粘合的东西分开,古今意义不同。“绸”,古代是“缠绕”的意思。《尔雅·释天》“素锦绸杠。”现代“绸”的常用意义是“绸子”,指薄而软的丝织品。又如《左传·桓公三年》:“凡公女嫁于敌国。”“敌国”是指与我地位相匹敌的国家,并不是与我相为仇敌的国家。《左传·僖公三十年》:“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行李”是指外交使节,并不是人们出行时所携带的衣物铺盖。《尔雅》:“凫,雁丑也。”“丑”是“类”的意思,是说凫是雁的一类。有人曾把“凫,雁丑也。”理解为凫是丑雁,词义理解错了。我们在阅读古书中最感困难的属于这一部分。第三、古今词义有同有异例如:“爱”,古今都有“喜欢”、“亲爱”的意思。但在上古“爱”字还有一个常用的意义项,是“吝惜”、“舍不得”的意思。《老子》:“甚爱必大费。”《孟子·梁惠王上》:“吾何爱一牛”这是现代汉语所没有的。“恨”,古今都有“不满意”的意思,但是古今词义所表示的轻重程度不同。古代汉语的“恨”主要表示“遗憾”的意思,程度轻。《史记·陈涉世家》:“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诸葛亮《出师表》:“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痛恨:痛心和遗憾。)现代汉语的“恨”却表示仇根”的意思,程度重。“骤”,古今都有“急速”的意思,但在古代汉语中,主要用来表示“屡次”的意思,《楚辞·九歌·湘夫人》:“时不可古今词义的演变是异常复杂的,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词义的扩大 词义的扩大是指演变后的词义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范围比原义的范围大。例如:“诗”,古代专指《诗经》,《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现代泛指一般诗歌,词义的范围扩大了。“河”,古代专指黄河。《诗经·魏风·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左传·成公十六年》:“晋师济河。”《庄子·秋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孟子·梁惠王上》:“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河内”指黄河北岸,今河南沁阳一带;“河东”指黄河以东,今山西西南部。汉代以前,“河”的常用义特指黄河。后来泛指一般河流。把一条河的名称扩大成为一般河流名称,由专称变为通称,今义把古义的范围扩大了。“齿”,古义是指排列在唇前的牙。甲骨文画的正是门牙。《墨子·非攻中》:“古者有语,唇亡则齿寒。”后来泛指牙齿。白居易《与元九书书》:“未老而齿发早衰白。”把门牙扩大成为牙齿,“齿”的词义扩大了。“响”,古义是指回声。《玉篇》:“响,应声也。”《水经注·江水》:“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贾谊《过秦论》:“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今义泛指一切物体发出的音响,概念外延扩展了。扩大,就是把意义范围扩大了。第二、词义的缩小词义的缩小是指演变后的词义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范围比原义的范围小。例如:“金”,先秦泛指金属。《左传·僖公十八年》:“郑伯始朝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日:‘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这里记载楚王赏给郑国的“金”,显然指的是“铜”,因为那时铸兵器、铸钟鼎都用铜。楚王担心赏赐给郑国的铜会用来制造武器,所以与郑盟誓。甲骨文中没有“金”字,金文中有了“金”、“铜”,但没有“银”、“铁”,郭沫若认为“铁”出现于春秋时期。到了“铁”、“锡”、“银”都出现以后,“金”就逐渐地专指“黄金”了。如《史记·文帝本纪》:“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金”词义范围逐渐缩小。(现在“五金”、“金工”、“金属”等复合词里的词素还保留古代词义的痕迹。)“宫”,上古泛指房屋。“宫”、“室”是同义词,先秦都指房屋。秦汉以后。“宫”专指封建帝王的住宅,如“阿房宫”、“未央宫”。现在除了某些叫“宫”的旧有名称外,只有某些化娱乐场所才称宫,如少年宫、文化宫。“宫”的词义范围越来越缩小了。“坐”,古代除当“坐下”的动作讲之外,还有“犯罪”、“因为”的意义,《曼子春秋·内篇》“王曰:‘何坐?’曰:‘坐盗。”《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上例的“坐”当“犯罪”讲。汉乐府《陌上桑》:“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杜牧《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上例的“坐”当“因为”讲。现在专指“坐下”讲,今义比古义缩小了。“丈夫”,古代指成年男子。《说文》“周制,八寸为尺,十尺为丈,人长八尺,故曰丈夫。”《韩非子》:“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战国策·赵策》“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后来只指配偶的男性一方,即“妻之夫”而言。概念外延缩小了,就是把意义范围缩小了。第三、词义的转移 是指词义反映的客观对象.由甲类事物转移到相关的乙类事物上去了。例如“坟”,古代本指高大的土堆或河堤。《方言》:“凡土而高且大者谓之坟。”《诗经·周南·汝坟》:“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沿着那汝水的大堤,砍伐那枝条树干)《楚辞·九章》“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大坟”是高大的土堆。远古,人死理起来并不堆土,故《礼记·檀弓》云:“古者墓而不坟。”后来,墓上堆土,就把这种土堆称为“坟”,于是“坟”也就指用土堆起的坟墓了。今义则把原来的“高大的土堆”、“河堤”转移到“坟墓”上来了。“豆”,甲骨文中形似高脚杯,是一种盛肉食的木制的高脚碗。《诗经·大雅·生民》“于豆于登”(盛肉于豆,盛肉于登。”)“豆”就是指这种器皿。后来,“豆”的意义转移到豆类植物及其果实上了。豆类植物,上古不叫“豆”,而叫“菽”。“脚”,原指小腿。中古以后,“脚”指踝骨以下部分,当“足”字解。今义则把原来的“小腿”转移到小腿以下的部位了。“兵”本指兵器。《说文》:“兵,械也。”贾谊《过秦论》:“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成语“短兵相接”之“兵”,都指兵器,今义是指士兵、战士,把“兵器”转移到持兵器的人,就是词义搬了家了,搬到附近的地方去了。第四、词义的褒贬色彩不同 风俗习尚和社会思潮的改变,往往引起人们对事物的爱惜与善恶评价的变化,从而影响词义褒贬的。由于风俗习尚和社会思潮的改变,从而影响词义褒贬的更替。有的词由褒义变为贬义,有的词由贬义变为褒义,有的由中性词变为贬义词。例如:“爪牙”,古代是指武将、猛士,是个褒义词。《国语·越语上》:“夫虽无四方之忧,然谋臣与爪牙之士,不可不养而择也。”《汉书·李广传》:“将军者,国之爪牙也。”“爪牙”的今义是指帮凶、走狗,成为贬义词了。“复辟”古代是指“恢复君位”,是个褒义词,现在是指“反动势力的复活”,成为贬义词了。“锻炼”,古代是指“玩弄法律对人进行诬陷”,是个贬义词,现在指“劳动锻炼”、“思想锻炼”、“锻炼身体”,“锻炼”成为褒义词了。“谤”,古代是指公开指责别人的过失,是个中性词。《国语·周语上》:“厉王虐,国人谤王。”“谤”的今义是指“诽谤”、“毁谤”、“造谣中伤”,成为贬义词了。“贿”,古代有“赠送财物”的意思,是个中性词。《左传·宣公九年》:“孟献子聘于周,王以为有礼,厚贿之。”“贿”的今义是指“贿赂”,即“用财物收买”的意思。成为贬义词了。这样看来,古今词义的异同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古今词义基本相同。有些词的词义没有什么变化,这不仅仅限于基本词汇部分的词。有些词,古今字书的注释大体相同。不仅单音词如此,复音词也不乏其例。早在《诗经》里就有芍药、梧桐、凤凰、仓庚、蟋蟀、苍蝇、参差、窈窕等词,我们阅读古书,按照现代汉语的意义去理解这类词,不会产生什么误解,但这类词在全部词汇系统中只占少数。第二、古今词义完全不同“揭”,古代是“高举”的意思。《诗经·小雅·大东》:“维北有斗,西柄之揭。”(箕星之北有南斗星,西翘长柄,向东远伸。)《战国策·齐策》:“于是乘其车,揭其剑。”后以“昭然若揭”形容真相毕露、明白清楚。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成语词典》把“昭然若揭”释为“明显得像揭开盖子一样”.这是不了解古今词义的差异而造成的误解。现代“揭”的常用意义是指把盖合或粘合的东西分开,古今意义不同。“绸”,古代是“缠绕”的意思。《尔雅·释天》“素锦绸杠。”现代“绸”的常用意义是“绸子”,指薄而软的丝织品。又如《左传·桓公三年》:“凡公女嫁于敌国。”“敌国”是指与我地位相匹敌的国家,并不是与我相为仇敌的国家。《左传·僖公三十年》:“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行李”是指外交使节,并不是人们出行时所携带的衣物铺盖。《尔雅》:“凫,雁丑也。”“丑”是“类”的意思,是说凫是雁的一类。有人曾把“凫,雁丑也。”理解为凫是丑雁,词义理解错了。我们在阅读古书中最感困难的属于这一部分。第三、古今词义有同有异例如:“爱”,古今都有“喜欢”、“亲爱”的意思。但在上古“爱”字还有一个常用的意义项,是“吝惜”、“舍不得”的意思。《老子》:“甚爱必大费。”《孟子·梁惠王上》:“吾何爱一牛”这是现代汉语所没有的。“恨”,古今都有“不满意”的意思,但是古今词义所表示的轻重程度不同。古代汉语的“恨”主要表示“遗憾”的意思,程度轻。《史记·陈涉世家》:“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诸葛亮《出师表》:“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痛恨:痛心和遗憾。)现代汉语的“恨”却表示仇根”的意思,程度重。“骤”,古今都有“急速”的意思,但在古代汉语中,主要用来表示“屡次”的意思,《楚辞·九歌·湘夫人》:“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吕氏春秋·适威》:“骤战而骤胜。”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今之‘骤’为暴疾之词,古则为屡然之词。凡《左传》、《国语》言‘骤’者,皆与‘屡’同义。”而现代汉语主要用来表示“骤然”、“突然”的意思。又如“池”,古今都是“池塘”的意思,而古代还有“护城河”的意思,这为现代所无。“国”,古今都有“国家”的意思,而古代还有“首都”的意思,这为现代所无。“色”,古今都有“女色”的意思.而古代还有“脸色”、“表情”的意思,这为现代所无。“树”,古今都有“树木”的意思,而古代还有“种植”的意思,这为现代所无。“馆”,古今都有“宾馆”的意思,而古代还有“宫殿”、“教学场所”的意思,这为现代所无。“除”,古今都有“除去”的意思,而古代还有“宫殿台阶”、“任命官吏”的意思,这为现代所无。池、国、色、树、馆、除等词,都是古今词义有同有异的词。学习古汉语词汇,要特别注意古今词义的异同。在异同的问题上,难处不在同,而在异;不在“迥别”,而在“微殊”。(王力《古代汉语》),我们要在古今词义的“微殊”上狠下功夫。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吕氏春秋·适威》:“骤战而骤胜。”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今之‘骤’为暴疾之词,古则为屡然之词。凡《左传》、《国语》言‘骤’者,皆与‘屡’同义。”而现代汉语主要用来表示“骤然”、“突然”的意思。又如“池”,古今都是“池塘”的意思,而古代还有“护城河”的意思,这为现代所无。“国”,古今都有“国家”的意思,而古代还有“首都”的意思,这为现代所无。“色”,古今都有“女色”的意思.而古代还有“脸色”、“表情”的意思,这为现代所无。“树”,古今都有“树木”的意思,而古代还有“种植”的意思,这为现代所无。“馆”,古今都有“宾馆”的意思,而古代还有“宫殿”、“教学场所”的意思,这为现代所无。“除”,古今都有“除去”的意思,而古代还有“宫殿台阶”、“任命官吏”的意思,这为现代所无。池、国、色、树、馆、除等词,都是古今词义有同有异的词。学习古汉语词汇,要特别注意古今词义的异同。在异同的问题上,难处不在同,而在异;不在“迥别”,而在“微殊”。(王力《古代汉语》),我们要在古今词义的“微殊”上狠下功夫。展开全文
在词义变化的过程中,指称义素和区别性义素呈现出变换、遗传、扩大和紧缩等不同的形态。今天出国留学网带来的论文就来浅谈古代汉语词义发展演变及其原因,欢迎阅读。浅谈古代汉语词义发展演变及其原因 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观里提到事物是发展变化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语言自产生以来,经过悠悠历史长河,由于不同的历史特征、社会环境,也处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之中。而语言内部的重要因素——词义,同样也处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之中。 词义演变原因: 1、社会的发展是影响到词义演变的最主要因素。语言属于社会现象。 从社会存在的时候起,就有语言的存在。语言是随着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语言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社会之外是没有语言的。因此,要了解语言极其发展的规律,就必须要把语言同社会发展的历史,同创造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密切联系起来研究。因此,考察词义的演变也必须与社会发展的历史紧密地结合起来。比如“民”,在殷商和西周时指奴隶。《尚书·多士》提到“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灭殷后,要把殷的一部分人迁到成周。此时,这些人已经成了周朝的奴隶,所以称之为“民”,又因为不服管束,称之为“顽民”。随着奴隶制经济的解体,封建制逐渐取代奴隶制,“民”由奴隶上升为自由民,社会地位提高了。“民”就有了“人民”、“百姓”的意思。此例充分说明了社会变化给词义带来的深刻变化。 2、古人的风俗习惯和对事物的认识与联想等,对词义的演变也有影响。 语言是一种系统性的事物,它深深受使用它的群体影响,无论是语言,语法,还是语义都具有约定俗成的特点。比如“羊”,古代认为是六畜中最具美味的佳肴,这种风俗习惯也在文字和字义上有所反应,出现了一批从“羊”得声的形声字和会意字,它们大多有“美好”、“善良”等义,如“祥”,从“羊”得声训为“善”。“善”从“羊”会意,训为“吉”。“美”从羊会意,古人既把羊看成是吉祥、美好的东西,它的词义经过经过抽象和引申,不少美好善良的品德和事物东都可以用“羊”来形容。比如《诗经·召南·羔羊》这首诗,比喻“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小羊称为“羔”。又比如“玉”字,本来的意思是“美石”。可是古人认为“玉”有五个美好的品德:仁、义、智、勇,因此士大夫都佩戴美玉以此喻德。《礼记·玉藻》:“古之君子必配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可见平时古代君子都是玉不离身,因此“玉”比喻为一切美好的事物。 3、词义的发展演变也有着自己的内部规律,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语言交际中人们对词义的选择性注意。 某个词在某一种语言环境中不断地连续使用,由于约定俗成的原因,会把一个较为广义的词的词义限制在其中的某一个方面上。而大多数事物或物件都是复杂的,它们由若干个可分的部分组成一个整体。这些部分中,有的部分与说话人要表达的思想有关,有的则无关。在语言交际中,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与谈话内容有联系的重要部分上。比如在古代汉语中,“臭”字兼有“香”和“臭”两个意思。《易·系辞上》:“其臭如兰。”此时的臭就是“香”的含义。孔颖达疏对“臭”字的词义变化训释得很好:“臭是气之别名,古者香气秽气皆名为臭。”在语言交际中,“臭”字由于经常表示臭秽之义,人们对这个意项又加以选择性的注意,所以“臭”字的词义也发生了演变。 古今词义的演变方式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词汇,它的意义在历史变迁中已发生了重要变化。首先我们必须要看清楚语言的继承性。因此,追根溯源,我们不能忽视了古代汉语词义及其演变过程。在我们现代词汇中,有这样一些词,它们的意义直到今天仍然是几千年的意义,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化。如“大”、“小”、“哭”、“笑”等,这些属于基本词汇,是词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语言继承性、稳固性的重要表现之一。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词,由于语言的继承性,今义从古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古今之间必然要发生关系。有些关系是比较明显的,有些关系却很隐晦。这些都需要我们日常积累并且认真分析。 词义的演变是异常复杂的,大致可以分为下面四方面。 第一、词义的扩大。词义的扩大是指概念的外延扩展,引申后的词义所反应的客观对象的范围比原来扩大了。例如:“诗”,在古代专指《诗经》,《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现在就泛指一般诗歌了。相似的字还有“江”、“河”。在古代,江、河都是专有名词,本指长江、黄河。如《公输》:“江汉之鱼鳖为天下富。”《史记·项羽本纪》:“项羽乃悉引兵渡河······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后来由特指的长江、黄河引申指一般河流,由个别到一般,词义的范围扩大。原来的专有名词“江”、“河”后来加上形容词表示,成为“长江”、“黄河”。“航行”一词,原来仅指在水上行走,现在也用来指飞机在天空中飞行。“花”原来指植物的花朵,都来扩大为整个植物,包括根、茎、叶在内。如“种花”,还有引申为动词“花钱”,相当于“使”、“用”的含义。 第二、词义的缩小。词义的缩小是概念外延的缩小,即后来的意义所反映的客观对象的范围,只是原来的一部分或是一个方面。如“宫”,上古泛指房屋。“宫”“室”是同义词,先秦都指房屋。秦汉以后,“宫”专指封建帝王的住宅,如“阿房宫”、“未央宫”。而现在除了某些叫“宫”的旧称外,只有某些文化娱乐场所才称宫。如少年宫,文化宫。“宫”的词义范围越来越缩小了。再如“丈夫”,古代指成年男子。《说文》:“周制,八寸为尺,十寸为丈,人长八尺,故曰丈夫。”《韩非子》:“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后来“丈夫”一词只指女性的配偶。“床”在古代兼指坐具和卧具。《说文》:“床,安身之坐者”,段玉裁改之为“安身之几坐也。”《木兰诗》:“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都是指坐具,现在的“床”,常指卧具,应用范围缩小了。 第三、词义的转移。词义的转移是指词义由甲事物转移到指称乙事物,甲乙两者之间没有类属的关系。例如“穷”,《说文》卷七说是“极也”,本义是“尽”或者“尽头”,引申为苦难或是走投无路;用作动词,则是“走到尽头”。《荀子劝学》:“蜷蛇无足而飞,梧鼠五技而穷。“《游褒禅山记》:“ 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 后来“穷”有贫乏之义,成为“贫”的同义词,词义就转移了。古代“穷”和“贫”是有分别的,“贫”和“富”对举,“穷”和“通”对举。后来,“穷尽”之义少用了,但残存于成语之中,如“日暮途穷”、“山穷水尽”、“穷寇莫追”等。再如“谢”字,《说文》:“谢,辞去也。”引申为“告诉”、“向·······说”或“引以为过”。《触龙说赵太后》:“入而徐趋,主而自谢。” 《鸿门宴》:“于是遂去,乃今张良留谢。” 《孔雀东南飞》:“阿母谢媒人:‘女子先有誓·······’” 后来引申为“感谢”,和“辞去”没有类属关系,词义就此发生了转移。 第四、词义的褒贬色彩不同。风俗习尚和社会思潮的改变,往往引起人们对事物的爱惜与善恶评价的变化,从而影响词义的褒贬。有的词由褒义变为了贬义,有的词由贬义变为了褒义等等。例如:“爪牙”古代弑指猛将,武将。《国语·越语上》:“夫虽无四方之忧,然谋臣与爪牙之士不可不养而择也。”《汉书·李广传》:“将军者,国之爪牙也。”而“爪牙”的今义确是帮凶、走狗,成为了一个贬义词。再如“复辟”,古代是指“恢复君位”,现在是指“反动势力的复活”。贬义成为褒义的也有,如“锻炼”,古代弑指“玩弄法律对人进行诬陷”,是个贬义词,现在指“劳动锻炼”、“思想锻炼”、“锻炼身体”,“锻炼”成为了褒义词。 第五、词义的虚化。词义的演变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演变还往往引起词性的变化。变化虽然复杂,但有一个主要的趋势。就是从实到虚。词性如此,词义也是如此。古代实词多,虚词少。现代汉语的虚词,绝大多数是从古代实词演变而来的。如“相”字,《说文》:“相,省视也,从目从木。”《易》曰:“地可观者莫可观于木。”《诗》曰:“相鼠有皮。”本义是仔细看,观察,引申为“辅助”,再引申为“互相”,再转化为无实际意义的词。《史记 淮阴侯列传》:“相君之面,不可封侯,又危不安。” (观察)。《游褒禅山记》:“主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也不能至也。”(辅助)。《指南录后序》:“日与北骑相出没于长淮间。”(互相)“互相”之义很弱,又逐变为没有实在意义。《孔雀东南飞》:“誓不相隔卿,且暂归家去。” 《失街亭》:“再拨一员上将,相助你去。”“相隔”、“相助”后面都带上了宾语,这样的“相”变成了没有实际意义的词。 关于词义的发展变化,一般都是采取“引申”说来解释。在上述词义演变的五种情况中,“词义的扩大”(义项增多)是主要的,它使词的意义越来越准确、精密,这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和现象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注意词义的演变和新旧词义之间的关系,可以使我们对词义有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从而在阅读作品时,对于某些不止一个意义的某些词,也就不至于用今义代替原义而产生误解。 论文小编精心推荐阅读: 开题报告 | 论文提纲 | 论文范文 | 论文致谢 | 论文答辩 | 论文格式 | 论文写作
古意:陶器总名。瓦今意:瓦片。古意:这些情况。如此今意:像这样。古意:即使。虽今意:虽然。古意:只。但今意:但是。古意:立即。还今意:还有。古意:平治水患。治今意: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