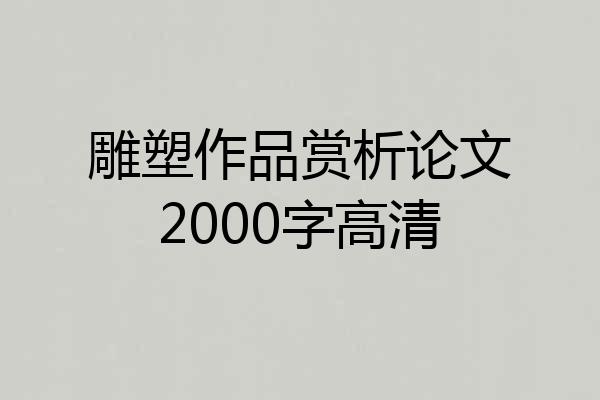jiaaa1993
jiaaa1993
谈对雕塑的认识 中国古代雕塑是中国古代艺术精华,中国古代雕塑在题材内容、形式风格、雕塑技法,以及所使用的材质上都具有鲜明浓郁的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如秦汉雕塑的粗浑、雄大,魏晋雕塑的健朗和潇洒,唐宋的丰富、端丽等。中国古代雕塑也充满了写意传神的特点,认真追究起来,很少有像古希腊作品那样符合现实中的真实标准的。它不习惯于玩雕塑作品的表面和细部,更喜欢那种由外在形象所引出的感觉、意境,引发出一连串遐想的空间,把人们引向一个艺术世界。 古代雕塑题材主要是陵墓雕塑、宗教雕塑和劳动生活及民俗雕塑。艺术门类有圆雕、浮雕、纪念性雕塑、案头雕塑、建筑及器物装饰雕塑等,雕刻材料也丰富多采,除了青铜、石、砖、泥、陶等材料外,还有玉雕、牙雕、木雕、竹雕等。 中国原始雕塑主要以人和各种动物形象的陶塑为主,人物形象大多是附加在实用器物上的装饰物,随意性很强,形象粗简、稚拙。商周时期的雕塑作品以青铜器铸造为主,青铜器上的纹案,主要有动物纹、几何纹。商代青铜礼器造型奇特,充满威严而神秘,崇高而怪异的美感。而从这时期考古挖掘中大量出土的雕塑中,唯不见有神像,这是世界雕塑艺术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西周以后,其风格趋于写实而富于理性。至春秋战国时期则变得繁丽、华美。商、周时期除礼器外,还有一些器物支架、底座等实用青铜器和石、骨、玉雕刻作品,或人物、或动物,皆造型巧妙,制做精细。 秦汉时期的雕塑空前繁盛,最具典型意义的是秦始皇陵兵马俑雕塑群。与青铜器神秘怪异的风格相反,兵马俑充满崇高阳刚之美。这数以万计的兵马俑,显示出对人的力量的肯定。人物、战马都与真实的一样大小,毫无夸张之处。以体量的巨大、数量的众多、形象的真实,产生着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西汉名将霍去病墓前的大型动物石刻,手法简练概括,于浑厚中显示着雄强的力之美。其中《马踏匈奴》再一次体验到中国雕塑艺术的写意传神的特点。那马虽然粗糙笨拙,但它仍然有一种灵动之势,那浅浅地雕刻的几笔就是马腿,它与马的上身连成一体,多余的没有雕空的石料根本不存在,有的是一个完整的马的形象。 汉代的厚葬风使动物俑和人物俑的雕塑作品众多,其造型古朴、神态夸张而强调动势。汉代世俗生活成为雕塑的素材,舂米、采芋、酿酒以及舞乐百戏等情景在汉代的砖画象中以浮雕的形式大量存在,宴饮、驱车、习射等土大夫的生活也得到了表现。 在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中,佛教最具有艺术性的。随着佛教的盛行,佛像雕塑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雕塑艺术的主流,著名的云冈、敦煌、龙门、麦积山四大石窟均开凿于这个时代。一般而言,北魏时期的造像在形式风格上受印度或西域式样的影响,庄严、浑朴,于静穆中显示着佛的伟力。南北朝的佛教雕刻融合汉族知识分子的审美时尚,形成了褒衣博带秀骨清象的新风貌。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雕塑的鼎盛期,其成就首先表现在石窟雕塑上,如龙门石窟奉先寺石刻造像。其雕刻手法流畅而娴熟,创造了完全民族化的造型风格,不仅体现着唐帝国博大、雄强的时代精神,同时也显示出唐人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雕刻技艺。如果说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在造像上还是模仿印度,那么到了唐代的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像》,中国雕刻家的技巧已经圆熟,对佛像雕刻艺术的精髓有了深刻的理解。卢舍那佛像已经是中国化的佛像了。 《昭陵六骏》是唐太宗陵墓前的浮雕,与兵马俑一脉相承,《昭陵六骏》体现中国古代雕塑的现实手法,没有失实的夸张,没有虚化诡异的造型,这些雕刻同样显示出对自然和人的力量的肯定。此外,最能代表唐代雕塑艺术水平的还有那些真实生动的三彩俑和四川大足石窟。大足石窟中各种经变故事中的普通人物更为生活化,现实化,不少作品也完全可以被视为普通人的肖像。 世俗题材的增多和写实风格的发展是宋、辽、金时期雕塑艺术的主要特点,山西晋祠、山东长清灵岩寺、江苏直保圣寺彩塑,都生动传神地表现了世人情态,有很强的写实性。辽代大同下华严寺的菩萨造像体态优美,神情含蓄,衣饰华美,大有唐塑遗风。此外小型泥塑,在写实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中国古代雕塑有一定局限性,中国的王宫贵族的帝王观和艺术观,与西方相比,同样是出于显威、歌功颂德的目的,中国的王宫贵族回避了直接塑造自己而采用了龙凤、狮子、麒麟等瑞兽以及仆人、军队、武士来烘托自己的伟大与神圣。同样,在佛教雕刻中,古代雕塑家最能发挥现实描写才能的只是罗汉,菩萨,观音,创作自由最为有限的是主佛。 古典雕塑可能很容易被人视为太旧,太传统,但笔者认为,尊重传统意味着承认艺术史的连续性,雕塑艺术需要不断创新探索,但任何创新都不是异想天开的标新立异,创新也意味着对传统的继承。当今传统艺术正受到西方现代主义越来越强烈挑战, 新的思潮要摧毁一切旧的传统,可是今天的艺术家为什么又纷纷回到被毁的废墟上寻找残存的传统文化呢?尘归尘,土归土。让我们踏上历史尘土,回味中国古典雕塑艺术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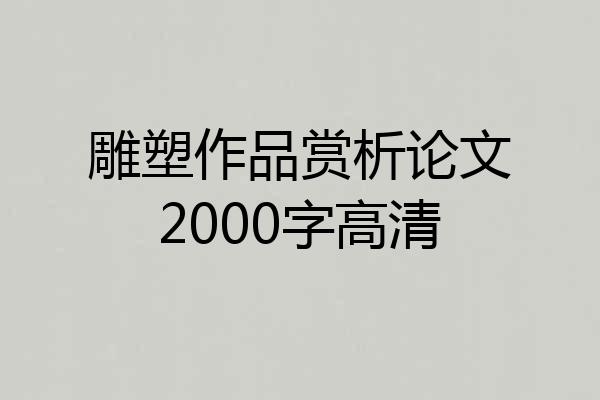
标准来看待它们,就能挑剔出解剖、比例不够准确,质感塑造不够充分等等不足,造成欣赏上的障碍。我们必须换一种眼光,使用我们自己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来欣赏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这样,当我们从敦煌菩萨,晋祠侍女、筇竹寺罗汉塑像上体会到“栩栩如生”这一句成语的含义时,就不是象欣赏西方古代著名雕刻,如欣赏教材常会介绍的掷铁饼者、拉奥孔群像和奥古斯都像等等那样,是个从形到神都准确得象真人一般的概念,而只是感受到一个艺术品所传达的人的生命力、精神状态和宗教境界等等形而上的东西。~~·五、中国古代雕塑语言精练,这是意象性衍生的另一艺术特点。中国古代雕塑始终没有发明西方雕塑的造型术(modelling)来精确地塑造物象,而多从感觉和理解出发,象中国画一般运用经济的语言,简练、明快,以少胜多而又耐人寻味,常常给人运行成风、一气呵成、痛快爽利的艺术享受。夸张乃至变形来强调人与动物的神韵,是普遍运用的手法,汉代四川说唱俑和霍去病墓石兽最有代表性。这些作品只是服从作者对物象的感觉和理解,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准确比例和真实效果,而是说唱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的表演神情以及虎、象、马、牛、野猪等动物的不同习性和旺盛活力。这样必须有所取舍,有所夸张变形甚至抽象,其效果更突出对象的特征,更具有艺术感染力,给人的印象更特殊而深刻。这一点和西方近现代雕塑有相似之处。西方近现代雕塑一反传统的写实为变形,追求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不被客观物象所役,使艺术创造更纯粹。中国古代雕塑实际上也是达到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这种艺术境界的。霍去病墓石兽采取“因势象形”的手法,充分利用岩石,自然的令人联想接近某种动物的形状,只进行最低限度的艺术加工,使石兽的造形显出空间的自由而不斤斤计较于形似。加工的语言有圆雕、有浮雕、也有线刻,是根据岩石形状与动物形象的双重需要加以多变性运用的。这种圆、浮、线雕并施的语言,在汉唐陶俑、历代石兽以及佛教造像中均可见到。它们使中国雕塑在精练中块面更整体,因而有时更具雕塑感甚至建筑感,例如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和龙门奉先寺唐代大佛,就是杰出代表。六、中国古代雕塑既然是意象性的,注重“以形写神”,必然也象中国绘画一样,注重头部的刻划。中国古人认为“头者精明之主也”。(《黄帝素问》)“头者,神所居,上圆象天。”(《春秋元命苞》)从原始时代起,人面或人头,在工艺装饰中就受到特别重视,这应是中国古代造型艺术发展为特别重视传神的原因之一。这种重视贯穿了几千年,直到今天,在民间雕塑和农民画中,头部仍是艺术家首要表现的部分。头部以外的人体部分,便被看作是从属的,较为次要的。这样,在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中,头大身小逐渐变成一种习惯造型,一旦头身关系处理不好,在视觉上便难免造成不舒服的特点,这是不必为古人护短的。然而优秀的作品常常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缺点中吸引转移集中到刻划精彩的头部来。这些头部看似没有西方雕塑深入,可是结构十分严谨。搞过雕塑的人都有体会,临摹西方雕塑易,临摹中国古代雕塑的头部却相当困难。它们不如西方雕塑结构准确分明,却另有一种完美性,神完气足,很不易临摹到那种境界。在头部以外,又用充满韵律的身体衣纹线条来发挥美感,使人受感染的不是比例结构的准确本事,而是传神美化的功夫。龙门奉先寺大佛、服侍菩萨与天主力士像都严重头大身小,但依然很美,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古代雕塑的这一特点。七、中国古代以“温柔敦厚”为诗之旨,这和中华民族的气质、生活条件、地理环境、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及其他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另的艺术也如此追求,表现在造型艺术上便是含蓄美、内在美。雕塑亦然,中国古代雕塑给人的感觉不象西方古典雕塑那样一览之下、历历在目,而是神龙露首不露尾、含不尽之意于象外。没有剑拔弩张,向外张扬的火气,而是象中国书画用笔藏锋那样将力量包裹在内部,给人更多品尝的余味。例如严阵以待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载歌载舞的汉唐女俑、孔武威风的唐代天王力士,乃至雄强猛厉的南北朝辟邪和唐代石狮,都有这种效果。比较一下掷铁饼者力量的紧张迸发和拉奥孔群象情绪的激烈发泄,就能够领会中国古代雕塑含而不发的美感特点。它是与其他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理想相一致的,就象西方雕塑与绘画的审美理想也相一致一样。欣赏中国雕塑时也许会觉得不如西方雕塑痛快顺溜,这就象喝酽茶和喝咖啡不同一样,不能相题并论。喝茶需要品味,如若不谙茶道,便永远进不了茶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