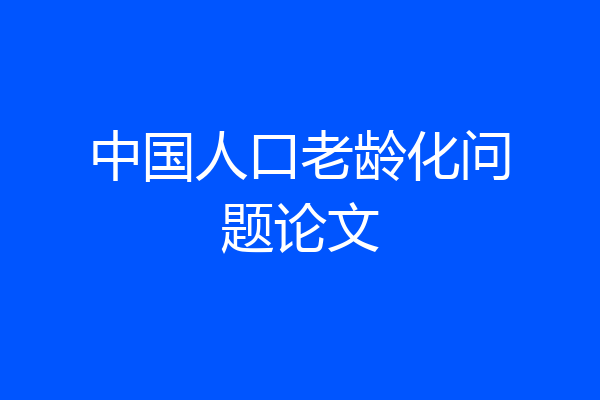手机用户
手机用户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从国际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来看,大部分国家都是在物质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才开始进入到人口老龄化阶段,相应地这些国家有足够的财力来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而本世纪初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时,物质财富积累则相对不足。2001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1%,按照联合国标准正式进入到老龄化社会,而当年人均GDP仅为6美元,不及德国、英国和加拿大的1/20,仅为美国和日本的3%左右,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2012年,中国人均GDP虽然大幅增长至2美元,但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多数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经济发展压力依然较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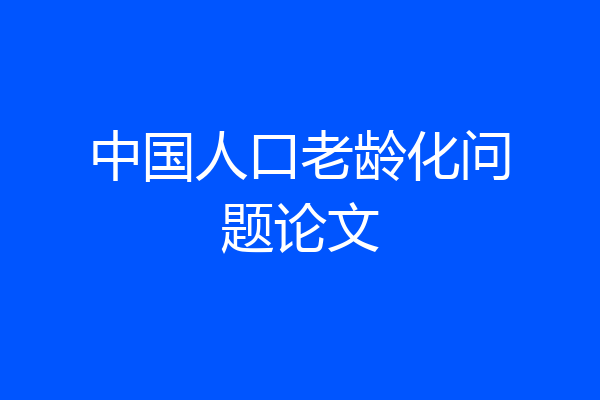
对老龄化的认识就是老人的人口总数很大,年轻人口劳动力人口逐年减少,最终会影响到方方面面。
回答
亲你好,很高兴为你解答这个问题,麻烦稍等一下哦,我正在编辑答案
提问
好的,谢谢
没有啊
回答
首先人口的老龄化是必然的趋势,由老龄化并不代表社会就不能继续进步了,社会依然在前进,手依然在进步,因为每个人都在努力做到更好,一个人创造的价值越来越高。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从应对人口老龄化及全生命周期的角度出发,要强调人的终身发展。因为无论是个体层面的衰老问题,还是群体层面的老年人问题,都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如果一个人在中青年时期没有做好准备,那么一旦进入老年期就无法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发达经济体,都会遇到,因此来说,做到应对人口老龄化,很多时候被迫做出延迟退休,或者是提高工作时间等途径来解决,其实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社会各方面不断进步和完善。
更多2条
第一:养老资金;第二,医疗保障;第三:人口稳定性……反正还有很多影响,你可以找些(老龄化研究)这样的资料去找下你的写作思路呗
一、当前老龄化研究中亟待商榷的认识偏差随着老龄化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学界已展开系统探索并取得较丰富成果,为正视老龄化挑战进行了必要的理论铺垫。而对于老龄化的具体应对措施与治理模式而言,描述性研究仍相对较多,单单针对老龄化或者它的某一方面进行论证和建议的研究取向相对普遍,且不同程度存在着将老龄化视为“问题”或“挑战”的倾向,这使研究成果相对聚焦于单项或局部的政策调整或调节,有一定工具理性特征,而与老龄化密切相连的其他问题或者同一问题的其他方面则经常被忽视,对整个老龄社会基本规律的系统研究和对政策体系的整合性研究仍相对欠缺。①事实上,人口老龄化及其影响具有较大的弥散性和渗透性,常常涉及一系列超越功能边界的非结构化公共事务,并形成诸多超复杂系统问题,其治理模式与政策安排必须基于这一特征展开。然而,所有的治理模式与政策变迁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其间更需要政府治理理念和社会主流观念的不断调适。因此,尽管老龄化议题近年来已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政府出于民生大计亦对其极为重视,但对其共识仍未普遍达成。随着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和社会转型的加速,识别并厘清当前研究和实践中的认识误区和理解偏差正变得愈加重要和必要,这将是老龄社会治理理念转型和社会观念更新的前提条件之一。 综合而言,现有老龄化研究与实践中亟待商榷的认识偏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对老龄社会的常态化欠缺共识,“悲观论”与“危机论”在研究实践中仍存在进入20世纪后,在现代化和现代性的逻辑作用下,人类寿命大幅延长而生育水平显著下降,两者叠加使得不同国家及地区的人口年龄分布普遍向老龄化倾斜。因而从本质上讲,老龄化是人类再生产模式转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由结果,它在任何国家和地区概无例外,区别只在于呈现之晚早和进程之慢快。2015年全球尚有115个国家和地区未进入老龄化阶段,但至2050年这一数字将可能骤降为33个。②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自2000年步入老龄社会后人口老龄化水平便不断提高,2010年“六普”时达到9%(65岁+)和3%(60岁+),而至2018年末这一数字已变为4%(65岁+)和9%(60岁+),其中60岁及以上的人口规模近5亿。学界对于未来中国老龄化发展趋势的整体判断亦基本趋同(见图1)③,老龄化已经成为一种长期不可逆转的基本国情。人口老龄化从本质上讲没有好坏之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还可被视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乃至社会发展的重要成果。然而遗憾的是,当前老龄研究与实践中仍充斥不少负面乃至悲观的情绪。这一方面源于社会大众在心理上的不适应,另一方面则是目前以中青年为核心形成的社会架构对老年人比例增多这一现实仍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匹配。这些“不匹配”更因“不适应”而被主观夸大,老龄化因而与“悲观”“危机”以及“负担”和“压力”画上了等号,尤其对于人口老龄化将造成经济发展延缓的担忧颇为流行。事实上,不少西方发达国家在尚未达到我国现有人均经济水平时已为应对老龄化而搭建起相对健全的全民社保体系④,因而用“未备先老”或“慢备快老”来形容中国当前的老龄化应对现状可能更为准确。此外,已有相当多的证据揭示老龄化对宏观经济发展并未带来不可逾越的挑战,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老龄化甚至与其经济增长显现出一定程度的正相关,中国最近几十年间的高速经济增长亦与其老龄化的发展进程相同步。这恰恰说明人口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的,不需要无谓地自我设障。正如戴利所指出“人们经常议论老年人口的保守性和反动特征,年轻人的进步和活力,这都是无稽之谈”⑤。(二)将老龄问题等同于老年人问题乃至养老问题,忽视了老龄社会治理的全民性和整体性老龄化的挑战常常被视为是老年人数量增多所引发的,老龄化的应对问题也常常被当作只是解决老年人的问题甚至只是养老问题,将这些议题过度聚焦于特定群体显然违背了现实逻辑。人口老龄化尽管暗含老年人口增多等数量性议题,但它在本质上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即人口年龄分布的结构性变动。老龄社会的老年人口比例尽管相较于传统为多,但依然是一个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群体共存共生的社会。而对于个体而言,老龄是其生命周期的必然阶段,这一年龄阶段与其他阶段的关联性在老龄社会的背景下更显其意义。已有大量研究表明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取决于其年少时的健康行为积累,养老金的收支平衡依赖于当前劳动力群体的劳动产出,老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而需要通过对不同生命周期人口的持续投资和引导而夯实。将老龄化议题过于聚焦在老年人群体既易产生不必要的社会焦虑,也不符合代际公平和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 针对这些片面的认识及解读,当前老龄社会治理研究与实践亦较多关注老年工作的开展和老龄事业的发展,而非老龄社会的整体性应对。⑥老年工作与老龄事业聚焦于如何为老年人口提供经济赡养、公共服务以及精神慰藉等支助,这当然是政府重视民生并为应对当前的现实养老压力而产生的一种自然选择,然而老龄化所意味的年龄结构变迁将涉及人口结构的各个层次和个体发展的各个阶段,仅仅关注老年人口显然无法全面应对老龄社会的诸多挑战。在此背景下,囿于体制资源等现实约束,较多的老龄化理论研究与政策探讨都聚焦于单一政策或部门政策的调整。然而在现实中,不同的部门往往专注于各自的功能和职能定位,部门之间职责交叉但界限不明确的情况时有发生,由于缺乏整合,出现政策冲突或政策衍生问题的例子并不少见,这更加剧了现有政策体系的碎片化,对其政策效能发挥反而产生了负面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对老龄化压力的社会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