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ujie296239
xujie296239
那你直接去找下(社会科学前沿)上的文献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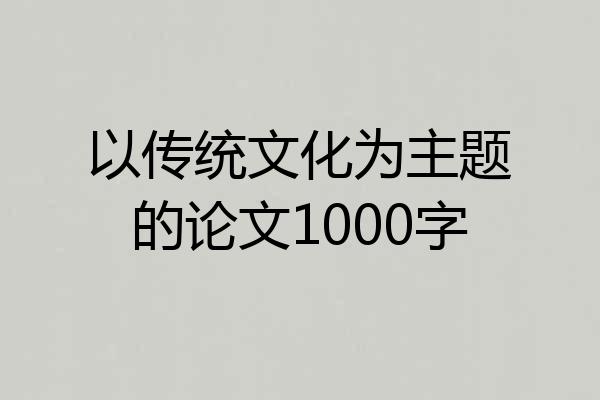
一首悠扬的曲子响起时,又一下子牵动了我的心。——曾记否,当年年轻貌美的外婆在那片广阔的天地间放声高唱起那一支支美妙的山歌时,年少的我是如此欢呼雀跃。而现在,我已经明白,早从那时候开始,就有一脉深远的文化深深地植入了我的血液里。外婆是土生土长的桂林人。瘦弱的身材、瘦弱的肩胛、瘦弱的脸形,是典型的当地人的特征。可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蕴育了人们的灵性,这灵性全镶进了那深邃的眼神里。它是源自人们的生命的尊重,对未来的憧憬。群山连绵起伏,山麓下细水长流,遍地绿树万荫、繁花似锦,这里的人们,一心一意把自己掩藏在大山那深深地皱折里。从春到夏,从秋到冬,默默地接受大山、小溪任意带来的温存与粗暴,一代又一代。村子里的人们不善言辞,白天逢人只会不太好意思地笑两下,来相互问好。男人从早到晚在田里不辞辛劳地耕作,扛着锄头,卷起裤脚总有干不完的活。女人们就在家里种桑养蚕,填补家用。顺着山脚一排延伸下去,对立的两排房子就是这几十户乡亲的家。白墙、青瓦。一切都是那么的安静和谐,水流的嗒嗒声,悬飞的鸟鸣声,一切又是这么的清新自然。外婆喜欢唱山歌,整个村子里的人都是。仿佛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全身上下所有的毛孔都立即通畅了,顿时感觉无比的畅快。傍晚时分,人们手里的活总算闲下来了。他们走出家门,男女老少,在那一时刻都抖落了身上的那份拘谨,一切都动起来了。村庄一下子热闹非凡。青年男女们你一句来我一句都是唱的对他(她)的思念,架着竹筏,一前一后,男的在前面用长长的竹杆往后拨浅溪水底下的石子来身来向前,女的则坐在后面一边痴痴地望着男子,一边用手击打溪里的水。山歌响亮动人,竟连群山都弯下了腰,侧耳倾听。成人们也有他们的唱词,借着山歌的调子,道出生活的甜苦交加的琐事以及对今年粮食收成大丰收的期待。“喂——”一声幽扬的歌声,便开始了对大山的所有对白。黝黑的脸上笑着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嘴巴慢慢张开——“李家的姑娘喂——嫁人了喂——”“今年的粮食大丰收了喂——”……一句一句,好像有唱不完的事,述不完的情。经久不息的歌声反复不停的激荡沉默的大山。坚定而有力,甚至是要穿越群山,飞到未知的远方。老人们也耐不住性子,也断断续续的唱上两句,神往地唱出曾经美好的回忆,还有田里辛勤劳作后胜利的丰收。小孩子不知道唱什么,只是不停地哼着熟悉的调子,踩着石子在水里不停地跑来跑去,高兴得忘记了时间的存在。而我曾经也是其中的一个,听着大人们放声尽情的歌唱,心里充满了形容不尽的喜悦。天渐渐地暗了下来,大山和远方都只剩下隐约的轮廓,从水里面弥漫开来的水汽慢慢的模糊了大家的视野。于是歌声也慢慢地消停了,只是回音还不时的耳边响起。一切又恢复了原样。人们悠闲地走回家休息,好像完成了一天的使命,他们便可以安安稳稳睡觉了,直到天明。……外婆的一生就这样平静而热烈的一路走来。经历过情窦初开的青涩、天真浪漫的爱情,虽然艰涩却很温情的家庭。这一切一如散落一地的珠子,全靠山歌这条带子将它们一一串起来,陪伴外婆走过生命的一程又一程。如今的外婆,像一只燃尽的蜡烛,只剩下捻下最后一点余温。可即使是这样,她也依然忘不了生命里的熟悉的旋律,说话也是借着调子。因为只有歌声才能将外婆内心所有的感情完全地表达。山歌,给了像外婆这样勤劳朴实的人们心灵上的鼓励。岁月,记录着一代代人一路走过来经历的辛酸与苦难。我们的祖辈们就在这里生长、繁衍、生根、死亡,究竟是多少轮回,才变成了今天的这番模样?只是山歌才能支撑着如水般柔弱的人们,而大山便是他们唯一的倚靠。厚重的大山给予了人们对生命的执着,对未来的永不放弃的精神。人世代代无穷己,我们更将经历这历史的回音。这脉自然的文化悠久的传来,必将延绵不断的传承下去。我们的祖先用他们辛勤的汗水浇灌着厚实的土地,用他们饱满的激情吟唱着千古的传奇。如今我的父辈们已走出了大山,离开了这曾经爱得深沉的土地。即使周遭环境的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可他们骨子里流淌的血液没变,它所凝聚的充溢着这朴实文化的坚定的力量,足以使他们保持心灵的本性,迎接未知的挑战。而我也是他们的下一代,身处异乡的我,已经渐渐淡忘了那个年代乡亲们的模样,但他们给我的影响必将会陪伴我走过一生,以及我身后的,世世代代。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传统文化伴我成长——文明美德伴我行有奖征文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和妈妈经常给我讲故事,一个个生动的人物,一幅幅让人感动的画面,陪伴我渡过了一个又一个幸福的梦乡。从那时起,在我的心中就种下了一粒种子,那是一粒传统文化的种子。“黄香温席”让我知道了如何感恩父母,“闵损芦衣”让我知道了兄弟之间需要相互关爱,“程门立雪”让我知道了尊敬师长……从那个时候起,我知道了,我们美丽的祖国有着怎样悠久的历史,又有着多少让人无限神往的文明美德。让我更加值得庆幸的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与《弟子规》这本书相识了,妈妈跟我说,你知道如何做一个好孩子吗?这本书会告诉你答案的。于是我带着疑问、好奇的心去拜读了这本书,“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当父母呼唤我们的时候,应当立即答应,不能迟缓,执行父母命令时应当立即行动起来,不能拖延偷懒。”啊,原来应该这样,在学习的同时,我的脑海不禁浮出这样的景象:我在玩电脑游戏的时候,妈妈喊我好几声,我却边打游戏边说:“你烦不烦,叫一声好了,还连续叫五声,真讨厌!!!”爸爸过来拍我肩膀,我很恼火地说:“你烦不烦呀,你看你看,我这一关没过去,又被别人打死了,就是你。”……我感觉自己的脸火烫火烫的,慢慢的,我象是老师批改作业一样从书中对鉴自己的错误,一次又一次的反思和自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