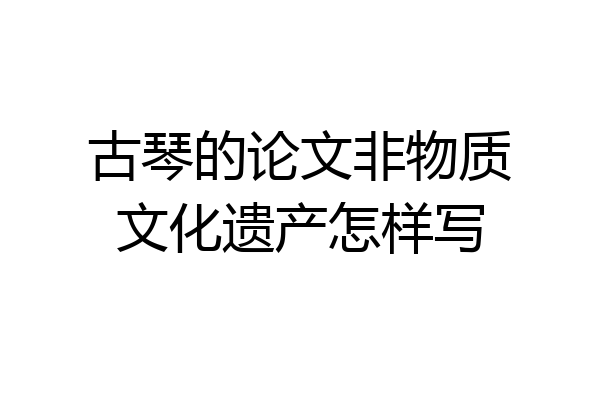田田hj
田田hj
古琴的文化内涵,在于它有着非常多元化的艺术特质,中国古代文人们对此有很多篇幅形容。 我国古琴艺术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它在历史上一直处于最为尊贵的地位,作为音乐艺术它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历史性、哲理性。是现在最古老的活着的成熟的音乐文化,影响极为广阔而深刻。其久远而丰富的音乐、学术、乐器遗产不但为今天日益增多的专业人士所关注,为日益增多的爱好者所欣赏、研习,还在2003年经我国申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公布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近二三十年,在甚大的范围内对这一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产生了极大的误解甚至误导。例如说“古琴音乐的特质在于静美”;古琴音乐的“最高境界”是“清微淡远”;古琴音乐“最简单的才是最好的”;“古琴音乐不是艺术,是道”;“古琴不是乐器,是道器”;“古琴是只弹给自己听的”以示高贵,反对把古琴作为人类文化艺术来对待,反对把经典琴曲演奏得鲜明感人,反对公开演出。这类或玄虚或神秘的说法在社会上、在互联网流传甚广,已令人们感到古琴艺术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神秘不可知,令人们或望而生畏或敬而远之,有害于古琴艺术的继承、保护、传播,故不得不辨。 我们从现存的两千多年以来的历代文献,包括当前琴坛所能听到的经典琴曲来看,都可以充分说明古琴音乐的特质,正如唐代琴待诏薛易简《琴诀》所示: 志士弹之,声韵皆有所主。琴之为乐,可以观风教,可以摄心魂,可以辨喜怒,可以悦情思,可以静神虑,可以壮胆勇,可以绝尘俗,可以格鬼神,此琴之善者也。 这是唐人对当时古琴艺术社会存在的总括,既可体现所承继其前的历史发展,也符合其后至今的古琴音乐的实际。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后曾经有把古琴艺术比喻为清高静雅的兰花的观点。但充满艺术光彩、崇高思想、坚定意志、真挚感情的《梅花三弄》、《流水》、《潇湘水云》、《广陵散》、《胡笳十八拍》、《忆故人》、《酒狂》、《离骚》等等诸多经典绝不与兰花相类。笔者经过长时期思考,于2000年尾形成了《琴乐之境》一篇,或可近于古琴音乐的实际: 琴之为乐,宣情理性。动人心,感神明。或如松竹梅兰,云霞风雨。或如清池怒海,泰岳巫峰。或如诗经楚辞,宋词唐诗。或如长虹骊日,朗月疏星。其韵可深沉激越,欣然恬淡。其气可飘逸雄浑,高远厚重。乃含天地之所有,禀今古之所怀。相依相比,相反相成。此其境。 以兰花为喻及静美说显然都与古琴音乐实际不符。现存最早记述古琴的文献见于《尚书·益稷》:“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 文字极为简短,却可以从中知道早在三千年前的夏商或更早些,曾把琴作为祭祀祖先的典礼乐器。既然是与其它乐器相配合来进行庄严神圣的敬祖典礼,所奏的音乐应是崇高稳重或明朗流畅。是对于先祖的怀念、祝愿、赞颂、祈求的心情表达,自无“静美”之可能。 距今2600年前的晏婴在论述他的“和”、“同”观时,以音乐为例说明成双组合、性质却相反的音声表现,以证“和而不同”,又要谐调于一体的“相济”才有意义。共列十组:“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其中“清浊、小大、短长、高下、出入、周疏”相依又相异的六组,所表现出的是变化着的音乐外形。而另外四组中的疾、乐、刚、速,则是音乐中明显的活跃、愉快、坚定、热情等内心感觉。晏子在此虽然没有指明是在说琴的表现,但在当时“八音”之中最被重视、最有表现力的是琴,其它乐器在当时是不可能有如此多的变化对比表现的。由此可知这时的琴的音乐实际存在着“疾”、“乐”、“刚”、“速”的表现的。 在晏婴此议的尾部说:“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进而强调琴瑟这两种经常共奏的最谐调的乐器,也必须和而不同。如果相互无异至“专一”,两者完全相同,则犹如用水去配合水,即“以水济水,”是无法成为美味的,是无人愿尝的,这样状态下的琴瑟共奏是无人愿听的了。则可以确定上面十种相反相成、和而不同的事例是举琴乐的实际表现。 《左传》鲁昭公元年(前541)医和曾说:“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慆心也。”主张君子是为了规范礼节而听琴瑟,而不是为了内心的愉悦。这也恰恰表明了当时的琴具有鲜明生动美妙的音乐性质、音乐表现,所以才要提醒君子不应忘记听琴、弹琴是自己的身份、地位的需要,而不可把琴作为艺术去欣赏、去求心理享受。这是医和从君子的品德要求来看琴,实是恰是提示对琴乐的艺术感染力的警惕。 公元前三世纪的吕不韦在他的《吕氏春秋》中所记: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 虽然我们不能就将它看作是春秋时期的伯牙与钟子期之间的演奏与欣赏的史实,但却可以肯定的是,公元前三世纪时人们对琴乐的了解和欣赏中得到了“巍巍乎”、“汤汤乎”的或雄伟、或豪迈的精神感受。亦即琴乐中已经具有“雄伟”、“豪迈”的形象和意境,并为千古以来人们所称道。 与吕不韦同时代的韩非,在他的《韩非子·十过》中记下了一则极具神话色彩的关于春秋时期名琴家师旷为晋平公弹琴而惊撼天地的故事: 平公提觞而起为师旷寿,反坐而问曰:“音莫悲于《清徴》乎?”师旷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闻乎?”师旷曰:“不可。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鎋,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今吾君德薄不足以听之,听之恐有败。”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愿遂听之。”师旷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云从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室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 虽然这应只是传说,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韩非的著述是他的思想、认识的反映,是当时社会存在所促成的。是韩非所处的公元前二、三世纪时琴乐给人们的影响所形成的。在这段记述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当时有极悲之曲,而且其惊人的感染力能对人的精神、心理造成极大的冲击和激荡。 生活于公元前156年至公元前141年前后的韩婴,在他的《韩诗外传》中有一项关于孔子向师襄子学琴的记述: 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子而不进,师襄子曰:“夫子可以进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夫子可以进矣。”曰:“丘已得其数矣,未得其意也。”有间,复曰:“夫子可以进矣。”曰:“丘已得其意矣,未得其人也。”有间,复曰:“夫子可以进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类也。”有间,曰:“邈然远望,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乐也。黯然而黑,几然而长,以王天下,以朝诸侯者,其惟文王乎?” 我们可以先不去探究这个记载所反映的学习中,一首乐曲是否可以那么具体的表现出文王的气质和形象,但可以相信的是《韩诗外传》撰者所处的时代,即公元前一至二世纪琴乐可以表现、已有表现“洋洋乎、翼翼乎”这类阔大昂扬精神和情绪音乐实际,即琴乐在这时的艺术状态是具有活力、有份量的。 公元前一世纪的桓谭《新论·琴道》篇记载了战国时期雍门周以琴乐打动孟尝君。先设想孟尝君死后,家国没落、坟墓破败的凄惨之境,令孟尝君先生悲痛。再以琴曲打动其心,以致“孟尝君歔欷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国之人也。’足证终于推动已被人生悲剧警示的孟尝君泪落涕流的琴曲,是一首表现鲜明、感染力强的悲哀之作。而在《琴道》篇的另一条记载“神农氏为琴七弦,足以通万物而考理乱也。”更是明指琴是可以反映对大自然的感受、对人生社会的体验的。 蔡邕(公元132—192)是东汉末琴坛大家,亦是历史上留有盛名的人物,在他的《琴操》一书中所载的四十七首琴曲中,有歌诗之《伐檀》为民生苦痛、世事不平而“仰天长叹”。有十二操之《雉朝飞》写孤独的牧者暮年之悲哀;有《霹雳引》的“援琴而歌,声韵激发、象霹雳之声”。河间杂歌之《文王受命》称颂文王的崇高功德;《聂政刺韩王曲》对聂政英勇坚毅之气的歌颂等等,都是当时活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琴曲,表现了浓厚而强劲的社会正义精神和昂扬情绪,皆是其时琴乐的实例。 嵇康(公元223—263)作为历史上著名琴人无人能予否定。其名之盛更因临刑弹《广陵散》而千古传诵。嵇康在他的《琴赋》中对琴所作的赞颂,明确的宣称是“八音之器”中的最优者,即最优越的乐器,并从很多方面加以充满感情的描绘:“华容灼爚、发采扬明、何其所也。”“新声嘹亮、何其伟也。”“参发并趣,上下累应,足甚足卓碟硌、美声将兴。”“(门达)尔奋逸,风骇云乱”、“英声发越、采采粲粲”、“洋洋习习,声烈遐布”、“时劫(提手加奇的奇)以慷慨,或怨(女字旁虎字头下加元旦的旦)躇踌。环艳奇伟,殚不可识。”“口差姣妙以弘丽、何变态之无”、“变用杂而并起,立束众听而骇神。”“诚可以感荡心志而发泄幽情矣”。这里所摘取的文句,元不呈现着被充满激情的琴乐所陶醉而激动不已的痴迷之状。这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发自深心的赞美与惊叹。无可怀疑的是他被琴乐所打动的真实记录。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艺术最为辉煌的时代,古琴艺术同样辉煌。在现存的一千多首与琴有关的诗作及不少其它文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古琴文化的诸多侧面。本文开始部分引述的薛易简《琴诀》所提出的,琴乐全面而深入地表现人在壮阔的自然环境中、在丰富的社会生活中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而且琴乐及其给人们内心带来的典雅、优美、鲜明、热情、壮伟的气质是其主流。谨摘几例为证:大诗人韩愈《听颖师弹琴》最为典型: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又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傍。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 诗中有“昵昵儿女语”的娓婉,“恩怨相尔汝”的鲜明,“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的壮伟;有“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的强烈变化;有“喧啾百鸟群,又见孤凤凰”的巧妙对比;有“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的灵动峻逸。诗人被琴乐震撼得感情强烈起伏,对于音乐给他带来强劲的思想冲击,产生了如同冰、炭同存于胸间,令人不堪承受的艺术感染,正与今天我们演奏和欣赏《广陵散》时最佳状态相合。 女道士李季兰的《三峡流泉》诗,写她听萧叔子弹琴的切实感受,一如当年住在巫山之下、大江之滨,日闻波涛之况:“玉琴弹出转寥夐,直似当年梦里听”。曲中有“巨石崩崖指下生,飞波走浪弦中起”之势,有“初疑情涌含风雷,又似呜咽流不通”的强烈变化与对比。这样的琴乐实际,自是其艺术本质的力证。 再如李白的《听蜀僧弹琴》诗中“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所展现的旷远豪迈之气。而韦庄的《听赵秀才弹琴》中“巫山夜雨弦中起,湘水清波指下生”隐隐有巫山神女入梦、娥皇女英涕泪的浪漫深切的痴情;“蜂簇野花吟细韵,蝉移高柳迸残声”的明丽优雅秀美之趣。他的《赠峨嵋山弹琴李处士》诗中的“一弹猛雨随手来,再弹白雪连天起”的大气磅礴,所展现的精彩演奏更令人惊叹不已,这样的琴乐自然是激情四射的。 成玉磵的《琴论》是宋代琴学文献中甚可宝贵者。其中讲到:“调子贵淡而有味,如食橄榄。若夫操弄,如飘风骤雨,一发则中,使人神魄飞动。”十分明确而有力的指出“操”、“弄”一类大型琴曲有能使人神魄为之激扬的震撼之力。此亦正与唐薛易简《琴诀》中“辨喜怒”“壮胆勇”的境界相一致。说明琴乐于宋代仍是与悠远的琴艺传统一脉相承,充满活力、灵气与豪情的成熟的艺术。 元代契丹贵族后裔耶律楚材,公元1229年被任命为相当于宰相职位的中书令。他的汉文化素养甚深。善诗文尤酷好琴。他幼时即“刻意于琴”,后在多年的追求中产生了极大的转变:“初受指于弭大用,其闲雅平淡自成一家”。但他却是爱栖岩的琴风“如风声之峻急,快人耳目”。虽然怀之,二十年之后终于在汴梁找到栖岩老人,可惜栖岩却逝世于将会面的旅途。幸好栖岩老人名叫兰的儿子的琴艺深得栖岩的“遗志”,而得以在六十天内以两人对弹的方法将五十多首“操”“弄”一类大曲的“栖岩妙指”“尽得之”。耶律楚材在他作于公元1234年的《冬夜弹琴颇有所得乱道拙语三十韵以遗犹子兰》中写道:“昔我师弭君,平淡声不促。如奏清庙乐,威仪自穆穆。今观栖岩意,节奏变神速。虽繁而不乱,欲断还能续。吟猱从易简,轻重分起伏。”可见耶律楚材所欣然受之的是激情奔涌的快速琴曲,起伏分明的强弱变化对比。而且“一闻栖岩意,不觉倾心服。”他未把平淡之琴奉为最高境界,而是将之与栖岩之峻急谐和以对:“彼此成一家,春兰与秋菊。”并且“我今会为一,沧海涵百谷。稍疾意不急,似迟声不跼”。可以相信这位元朝贵胄是极有音乐修养和艺术气质的文人。在他另一首专写弹《广陵散》的长诗中又一次直爽而有力的写上了他对充满激情的音乐表现的巨大感动:“冲冠气何壮,投剑声如掷。”“将弹怒发篇,寒风自瑟瑟。”“几折变轩昂,奔流禹门急。”“云烟速变减,风雷恣呼吸。数作拨刺声,指边轰霹雳。一鼓万息动,再弄鬼神泣。”所描绘的形象和感受明显与薛易简《琴诀》、韩愈、李秀兰之诗作完全相一致,更与我今天所演奏的《广陵散》的音乐表现相吻合。 虞山琴派的出现是明代琴学琴艺的一个伟大的丰碑,其创始人严天池的历史功绩所形成的日渐广阔的影响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一些人将虞山琴派归纳为“清微淡远”,并不符合客观的实际存在。我们认知和讲述虞山琴派的艺术风格、琴乐思想时,必须以严天池先生自己的著述为依据,即他在《松弦馆琴谱》所附的《琴川汇谱序》中以肯定语言所提出的:“琴之妙,发于性灵,通于政术。感人动物,分刚柔而辨兴替”。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明显是与薛易简《琴诀》中所说的“可以观风教”、“可以摄心魂”、“可以悦情思”、“可以格鬼神”的艺术性表现相一致的。 严氏指出“琴道大振”的琴乐表现是“尽奥妙,抒郁滞,上下累应,低昂相错,更唱迭和,随性致妍”,则是进一步明确其琴乐在艺术表现上深刻、精美、通畅、明朗,演奏技巧上丰富灵动,而求达到琴人相和、得心应手,以入美妙之境。这是严天池先生琴乐观念明白而肯定的宣示,怎能无视? 明末清初琴坛出现的艺术奇峰徐青山,在他的《二十四琴况》中详细地从各方面提出了琴乐的审美取向及其途径。其中属于悠然平缓范围的是:和、静、清、远、淡、恬、雅、洁、润、细、轻、迟十二项。另外八项:逸、亮、采、坚、宏、健、重、速属于热情、浓郁、雄健、强烈范围。而其余的古、丽、圆、溜,则在这两个范围的意境中都可兼有。可以看出徐青山的《二十四琴况》所反映的琴乐实际表现及美学观念的取向中可见热情、浓郁、雄健、强烈占有三分之一比例,似乎居于少数状况次要地位,但属于悠然平缓范围的恬、雅、洁、溜四项也是具有“发于性灵”而能“尽奥妙,抒郁滞,上下累应,低昂相错,更唱迭和,随兴致妍”之功的,和艺术真实本质扣动人心魄的力量是简单数量多少不能影响的。 已故大琴家管平湖先生之师杨时百是一位清末民初跨十九、二十世纪的伟大琴师。他所撰辑的《琴学丛书》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艺术价值、历史影响。他教授成琴坛巨人之一的管平湖先生对中华文明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杨时百在他的巨著中曾有用“清、微、淡、远”四字表述严天地的琴学宗旨。但他接着强调了“徐青山继之,而琴学始振”,并将徐氏的二十四况加以引述。同时指出那些否定琴乐“感人动物”,否定琴乐“发于性灵”、“随兴致妍”,而忧心的责难其时“声日繁、法日严、古乐几亡”者,否定琴乐在继承传播中的发展,否定艺术的发展所推动而丰富完善起来的演奏方法和理论。他们认为所想的古乐已临灭失的境地。杨公取笑这种人,称“下十成考语”的门外汉都“未有过于”他们,并且进而说这种人就恰是“文字中之笨伯”。 要想琴乐表现“可以壮胆勇”,“可以辨喜怒”,可以表现仁人志士的正义、坚强、雄伟、激越之情,就必须有充份的音量、有强弱变化幅度,故而音质佳而有大声者才是上等良琴。杨公告诉我们“有九德然后可以为大声”,并征引元代陶宗仪所著《琴笺》说,在古代“凡内廷以及巨室所藏,非有大声、断纹者不得入选。”杨公进一步指出实例:“武英殿所陈奉天故行宫数琴及宣和御制乾隆御题者,皆有大声也。” 至此,已可相信一系列文献所展示的古琴音乐的艺术存在、艺术观念,是一脉相承的,是全方位寄托和反映人们的真诚、善良、美好的思想、感情、生活。显然能达到这一目的琴乐表现才是最高境界。 同时从古琴音乐自身来看,不管是传世琴曲还是近五十多年来,经过时间检验被社会文化、学术所肯定的古谱发掘,即打谱的成果,同样有力地证明古琴音乐的特质绝不是“静、美”两字。“清、微、淡、远”这一清末才出现的观念可以是一种欣赏取向、思想类型,但不是最高境界,也不是一种根本的客观实际。千百年被广泛传播,有着崇高的文化地位和深远影响的经典琴曲,如《梅花三弄》、《流水》、《广陵散》、《胡笳十八拍》、《潇湘水云》、《渔歌》、《酒狂》等等,都是呈现着鲜明生动而强劲的艺术美,或热情、或浓情、或深情、或豪情,其感染力“动人心、感神明”恰可当之。都雄辩地证明着古琴是有着充分艺术性,而且是具有文学性、历史性、哲理性的活着的古典音乐。否定古琴音乐是艺术,否定古琴是乐器,既不合乎客观的历史存在,也不符合今天古琴艺术在人们心中所产生的并日益增加影响的现实。同时如果硬是把这些经典琴曲弹得“清、微、淡、远”,必定令人不知所云。而如果都把最高贵目标定位于古琴只弹给自己听,不许传授,不许演出,那要不了太久,古琴行将灭绝,虽然这是不可能的,却是不可不反对的。这种主观臆造的理论指导的行为是不能不妨碍古琴艺术健康的保护、继承、传播的,因而必须明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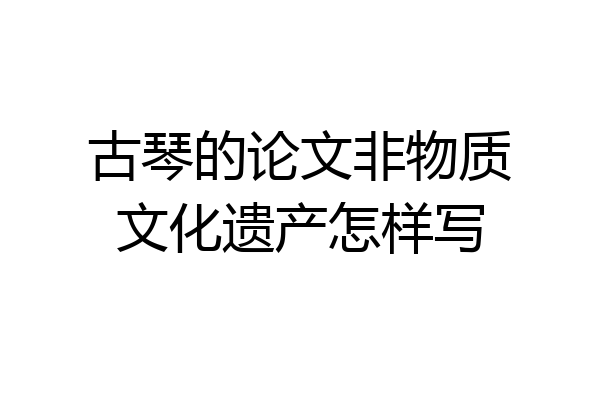
“音之起,由人心声也”一句简单的话却蕴藏着音乐中无限的情感,并且在这种情感中赋予音乐无穷的想象空间。 “古筝演奏”用一种动静相结合美的演奏形式来表达绘图式的美妙音乐意境,使听者在欣赏的过程中得到纯美的精神享受和意境体验。听者欣赏的过程中也是演奏者表达的过程。怎样等让听者“情动之中”?这样能让听者品尝到音乐中的美感?这是演奏者必须用心思索的两个问题。 我们在思索这两个问题前再次了解一下关于“艺术”追求的过程。“艺术”也称“异术”。之所以称为“异术”是因为所有的艺术表达带给欣赏者的感官刺激和精神享受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去欣赏器乐作品《百鸟朝凤》一样,有一千个欣赏者就会有一千种百鸟朝凤的不同景象呈现在我们脑中。在艺术表现和艺术体验的过程中它是千变万化的,同时也是美妙的。在音乐的演奏中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能用对与错去区别它,只能用我们真实的个人情感去品尝它,咀嚼它,赋予它定义。 “古筝”一种表达大自然情感及至入微的乐器,它那似水的音乐和自然的五声音阶微妙的表达着大自然与人之间的和谐。曾经看过明代的文学家、音乐家徐上赢《溪山琴况》他将古琴演奏的原则分为“二十四况”即“和、静、清、远、古、淡、恬、逸、雅、亮、采、洁、润、圆、坚、宏、细、溜、健、轻、重、迟、速。”在我看来古筝演奏过程中的技巧也可以依照这种准则。这些无形的纯技巧和意境性的词汇字意简洁、明了,但是把它们用于有形的实际演奏过程中却不简单。演奏者必须掌握每一种正确的演奏指法和技巧。只有掌握了指法和技巧才能正确的控制力度、速度、节拍和旋律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琴音合一,物我合一”的最高演奏境界。这也是指最基本的演奏织本。 每一位演奏者在演奏前须先了解自己演奏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和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只有了解了这些才能更好的理解到乐曲中的情绪表达和情感变化。因为理解作品思想是控制作品演奏情绪的基础。在了解了作品的思想后,我们便要分析全曲的曲式结构,从引子、开头、展开部、高潮、结束。把它们细致的划分开,分析每一部分的变化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中演奏者要很好的用情绪去把握力度和速度,我们知道如果作品中缺失了跳跃感,那么作品必定没有激情,平淡无味。所以演奏者应该在脑中有一种真实的情感体验。不管是表现肢体语言、表情语言、还是旋律韵味,都是演奏者在时间空间里用准确的演奏形式所表现的音乐。在这个演奏过程中演奏者要学会“无意识情感变化”就是说不要刻意的根据“环境”和“心境”去改变作品的情绪,也不能脱离作品的思想主线,需把情感和技巧相结合。同时也不能缺失演奏自身的情感表达。很直白,就像我们要表达哭泣时,用情绪控制着技巧、肢体、还有情绪本身的高亢激昂变化过程,这是很清晰的一种情绪表达。“演奏者给予作品第二次生命”就是这样理解的。 “作者”用灵感赋予音乐生命和意义。“演奏者”给音乐穿上了五颜六色的情绪外衣。“欣赏者”给音乐建造了无数个停留的心房。不管是音乐的作者,演奏者还是欣赏者都是对音乐艺术情感本身的“再创造者”,也是对艺术中“自然美”的再创造。这些再创造不是自发偶然形成的,它们有着特殊的意境效果。这种特殊的意境使欣赏者带着一种情趣去感受音乐。就像有很多听众在听《高山流水》时会置身于山水之间的狭义感、在听《将军令》时会有置身于杀场激昂澎湃感,之所以会身临其境是因为演奏者在演奏过程中用个人的情感理解了作品中的思想精髓,并惟妙惟肖的表现出来了作品的性格。因而能感染着,带动着欣赏者的情绪。这便是“音之起,由人心声也”的意境效果,也是演奏者的表达效果。 音乐是美的,演奏音乐和享受音乐是追求美的过程。用美的形式——演奏,去追求美的内容——作品,去感受美的思想和情感——欣赏。这是音乐本身一个完美的整合体。音乐演奏过程也是审美体验的过程,在动与静的肢体语言中我们倾听着,感受着,追求着生活美,同时音乐表达的情感带给我们生活中真实的情感意境和绘图式意境。
偶然性。。。可以就演奏中依照个人当时的心境、情绪不同而表达出的不同演奏效果进行讨论吧。。。古琴的演奏确实有很偶然的地方,因为古琴的乐谱没有像五线谱那样的标示节奏的体系。古琴乐谱用的是一种叫减字谱的体系,这个体系里表达节奏是用诸如“徐”、“缓”、“急”这样的字眼。这种模糊的表达,不同的人又不同的理解,所以在表现音乐的时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特点。古琴的演奏中吟、猱的使用也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吟、猱的幅度和次数虽然有限定,但是任然会因为弹奏者即时的心理感受而产生变化。另外,情绪对乐曲的表现也有影响。心情好的时候也许会急促流畅、有跳跃性;心情坏的时候也许会缓慢哀怨。这都是因人而异的。以上
琴德精神与大学生的“为学” 古琴是我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瑰宝,从先秦时代起,他便在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康盛赞:“众器之中,琴德最优”,古琴在文人阶层世代相传的结果,使得其具有了超越纯粹乐器的地位而获得了丰富的精神内涵。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面对古琴时,常常面对这样的困惑,即:古琴本是一样乐器,其研究应当属于音乐史的范畴,但古琴的发展、成型、流传、研究又对人们的精神生活有莫大的影响。只要我们面对古琴,就无法割断其与文化母体之间的脐带而奢谈其音乐史上的存在价值,亦不能将之作为纯粹的文化现象而剥离其具体音乐环境。在此基础上,古琴的音乐精神是一个综合体,只有从跨学科的角度进行多维观照,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这一文化瑰宝在今天的存在价值。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文化高峰,也是古琴音乐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在宋代,文人阶层将古琴纳入他们政治理想的一部分,把古琴音乐看作“三代之治”的理想社会的影子。在积极实践的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探讨与总结了古琴音乐的信念。古琴流传至今,不失其本身蕴含的精神,对当代大学生而言,虽然面临着许多教学有损的情况,我们也可以从琴德精神中得到感悟,从琴德精神可以学到古代人文高尚情操,对大学生“为学”有不可磨灭的意义。 一、琴德精神与“为学”的关系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为学的精神显而易见,人们无论从事何种事业,其原因不外乎:一是自己的爱好,能使自己获得身心享受;二是能从中获得物质回报。作为非职业化的业余爱好者,他们绝大多数是为了第一个目的去学习古琴艺术的,在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中,他们大多不会去想借此要获得特质上的利益,相反还要自己花钱学琴。“为学”是古琴爱好者学习古琴艺术的动力,也是当代古琴艺术赖以生存普及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