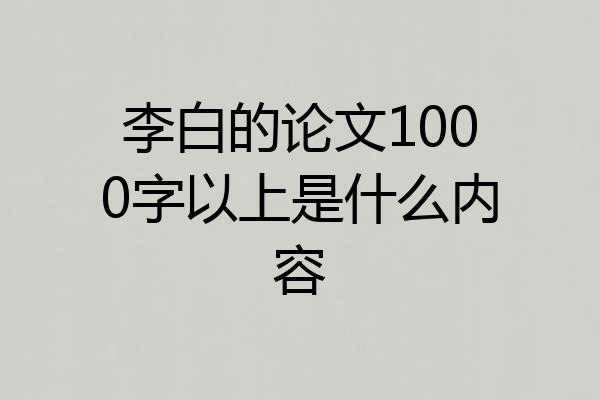卧室孤独
卧室孤独
桃花潭在今安徽省泾县,据记载它“深不可测”。李白游桃花潭时,曾受到当地乡民汪伦的款待,临离开时汪伦又赶到潭边相送,李白便即兴书写此诗赠给汪伦。我们现在用“情深似海”之类的词,已不觉新鲜了,但在唐代,李白即兴指潭水喻深情,则是个创新,因而令后人赞赏。问题是:李白是名动天下的大诗人,而据说汪伦只不过是一介乡村青年,且只是在李白游桃花潭时偶尔结识,那么,李白对汪伦如此深情热烈的赞颂是否有足够的感情内蕴呢?“深不可测”的桃花潭犹不及“汪伦送我情”该不会是诗仙虚与委蛇的应酬夸张吧?其实不然。细揣诗意,李白是把汪伦对自己的毫无私利之心的纯洁的友谊同世态炎凉相对比,是有着丰厚的现实生活感受作为基础的。李白这人,有大志,也有大才,诗名早就响震天下。但因他禀性兀傲,不愿阿附权贵,低眉俯首,因而长期遭受排斥,很不得志,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有着深切的体验。这次,他游桃花潭一带,自然会结识许多当地人士,但在离开时,却只有汪伦组织了一队人唱着歌,用脚踏着节拍前来热烈送行。这自然使潦倒失意的李白深为感动。当然,作为一首短小的绝句,他只能如此含蓄地写,因此,只有细加品味,才能体会到。“李白乘舟将欲行”,写诗人登舟时有所期待,而又惘然若失。句首直呼己名,含有一种深沉的感叹意味,犹如说:李白呀李白呀!“将欲”这两个字读起来是很感滞重的,似乎连招呼船家起程这样简单的事还得狠狠心才行。他为什么心情这样沉重呢?可以想见的起码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舟”为小船,当不会有许多人同行。“行”有“往”义,但不象“前往某地”那样有明确的目的地;有“去(离开)”义,但也不强调离开某地。这样看来,诗人用“行”字是为了表现一种欲行不行的矛盾心态。为什么呢?试想,诗人将要乘一叶孤舟继续他的漫游,在漫长的旅途中,其孤独可想而知。此时,他回望桃花潭岸边,这些天来所见之美景怎会不使他恋恋不舍?但终究是要离开了。这就会令人深深感叹。其二,诗人性格豪放,喜结交天下豪杰。此时,若有好友相送,金樽清酒,一饮“三百杯”,无论是放歌还是悲吟,总能渲泄胸中郁郁之情。可现在,孤零零地悄然离去,心中自然深感失望和怅惘。总之,第一句写诗人欲行不行时的怅惘,为下一句蓄足了情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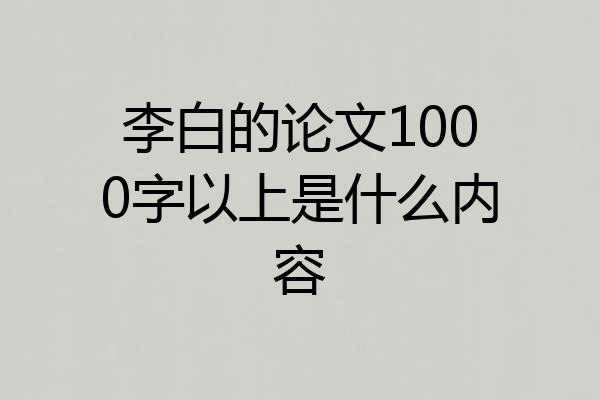
在大唐多若满天繁星的诗人中,李白是唯一被人们誉为既有侠肝义胆,又有仙风、道骨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传奇的一生,豪放飘逸的诗风,确实给人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使我们一说起李白,就可以想见一个飘然不群的诗仙形象。 其实自贺知章称李白为谪仙人起,李白的形象就定型了。然而这种定型化了的诗仙形象,也使人们与李白产生了一种近乎膜拜者与偶像之间的距离,一种雾里看花、云中观月的可望而不可及的隔膜限制了我们走入李白心灵的殿堂。 现在让我们走进李白的思想。李白的一生是复杂的,他一方面接受儒家“兼善天下”的思想,要求济苍生、安社稷,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道家遗世独立的思想,追求绝对自由,蔑视世间一切。他还深受游侠思想影响,敢于蔑视封建秩序,敢于打破传统偶像。儒家思想和道家、游侠本不相容,但李白却把这三者结合起来。 李白生平浪迹天下,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他尚武轻儒,脱略小节轻财好施,豪荡使气。这就养成了他崇尚英雄的性格。反映在诗歌中,他从无数古代英雄的风度,气派中吸取力量,把现实的理想投影到历史中去,从而在诗歌中建立起英雄性格的人物画廊。他歌颂草泽,际会风云的英雄,如《梁甫吟》,写太公望:“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八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歌颂视功名如草芥的义士。这反映了他敢于反对封建秩序,不畏强权的游侠思想。 在李白的身上,兼备了儒道侠禅各家的特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儒家的傲岸坚强;“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道者的避俗离浊;“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侠者的任性狷狂;“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禅者的玄思独绝。真是难以想象,在一个人的身上,怎能呈现出如此丰富的景观,且并不是流于表面,而是从心灵深处透出来的一种融合万物,顺应自然的美。也许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也或多或少的受着各种流派的影响,各种思想在我们的头脑中交锋,有的被杀死,更多的是在冲突中走向融合。或者说,根本不存在各种思想流派的分别,他们本来就是构成热的整个思想的各个零件,就象万物组成了世界的自然和谐。人为的硬生生的割裂并不是一种客观的态度
一篇关于李白的论文 李白的文化性格与待诏翰林政治失败漫议 诗人李白的一生,可以说始终都是以追求政治上的成功为其毕生奋斗目标的,而天宝初受玄宗征召并被命为翰林待诏,则可说是最接近政治成功同时又与成功失之交臂的一段经历。从天宝元年秋奉诏进京,至天宝三载春离京,其实际居京的时间仅一年半左右,旋即被“赐金放还”,离开了长安这个政治中心。就李白的一生而言,这次进京的荣耀与离京的失落,不仅构成了他终生难以磨灭的记忆,而且其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他后来的命运。对于这样一次最接近政治成功却又以失败告终的经历,不论是倾慕李白的同时代人,还是后代热爱李白的读者,无不表现出某种同情、慨叹乃至痛惜,并从不同的角度为李白的政治失败做出诠解。但是,如果将李白的从政方式放在盛唐政治文化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则可以发现李白的政治失败,从一开始就具有某种必然性。生活于盛世的诗歌天才的政治落魄,实际上凸现的是一种由文化疏离与冲突所造成的文化性格的悲剧(1)。 一 就李白的仕进道路来看,一个众所熟知的事实是,李白没有像一般士子那样,试图通过科举之路进入仕途。他从一开始就有着与众不同的选择,这就是希望以奇人名士的风采耸动天庭,进而直取卿相,甚至幻想成为帝王师式的人物。从李白天宝之前的行迹来看,他的一切活动,似乎都是围绕着培养自己的名士声望而展开的。 在中国士文化传统中,“名士”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并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重大影响,大约始于东汉后期(2)。桓、灵之际,当宦官、外戚干政造成东汉王朝政治的腐败与黑暗时,士人以对黑暗政治的对抗与批判,展示了其独特的操守,从而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形成了一批虽遭迫害但却在个人品格上受到尊敬与仰慕的名士群体。《后汉书·党锢列传序》即云:“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窦武、刘淑、陈藩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故、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以精神品格的卓异而著称的名士群体。至魏晋六朝,名士在社会政治与文化领域仍很活跃,虽然由于时代的变化,他们所呈现的精神风貌与其品格内涵已有所不同,但却仍是作为政治与文化的精英而受到士林的宗尚的。据《世说新语·文学》载,当时袁宏曾作有《名士传》一书,其书今不传,详细内容无从得悉,但刘孝标在为《世说》作注时则云:“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浚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可以大致了解其时名士的概况。《世说新语》一书,记录的多是汉末迄魏晋名士的言行,除上述刘孝标注所提及袁宏《名士传》中的人物外,还有其他一些人物,也常受到称赏,后世士人所乐道的魏晋风流,就是由这一群魅力独具的名士构成的。这些名士,也许性情、思想、趣味、作风不同,但他们之所以成为名士,原因却并不复杂,那就是一定要能够超越世俗的平庸,显示出自己精神、品格或才性上的迥拔流俗,而率性、洒脱乃至任诞,又往往是他们最显著的标徽。也由于此,由对名士的崇拜,甚而导致一些人视任诞、放浪为名士,“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世说新语·任诞》)。但总体看,魏晋六朝名士群体的个体风貌并不相同,其或者才华超群、或者潇洒风流、或者任诞不羁、或者品德高尚,而不论何者,都构成了他们赢得士林声誉并为朝野所瞩目的重要因素。 大致也是李白谪仙人称号出现后,中国人对谪仙特征的理解。但这已与唐前有关谪仙形象有了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由于谪仙人李白的出现,原来的谪仙观念已被重新改写增加了新的内涵。人们对它的认识与理解,已脱离了仙传文化的传统语境,而更多地带有了由李白所产生的直觉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