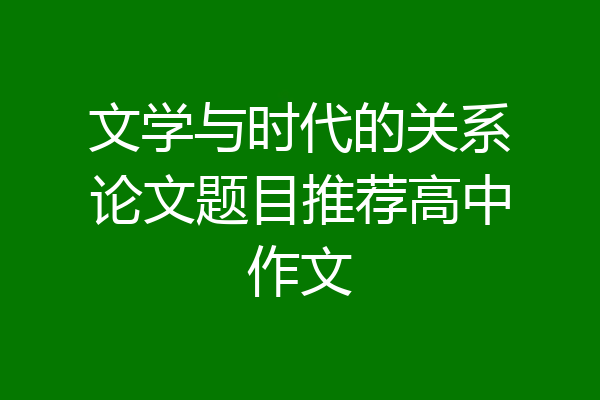whhit523
whhit523
我喜欢文学,因为从文学中,我获得了很多很多,那是在生活中很难实现也无法实现的。文学与我的生活是那么的密切。当我内心无限烦闷感到无限痛苦,当我想把内心积郁很久的东西表达出来时,当我想宣泄的时候,我开始写字,开始发泄。我像一个精力旺盛的泼妇一样把内心那些对我的身与有害的心毒素一点点抖落出来,吐到空旷的空气里去,让它慢慢消失。当内心那些繁杂的东西没了,发现全身是多么的舒服,像沐浴在阳光中一样,发现,原来文字的力量那么大,像洗涤剂一样,把内心的杂质全清除掉。 当我一个人远在异乡漂泊,当我的内心渐渐孤独寂寞找不到归宿时,当我想起远方头发渐渐发白的母亲和眼睛渐渐浑浊的父亲时,我也选择上了文字,选择上了笔和纸。我把温暖的思念写在纸上,一笔一笔,工工整整,我把对母亲无限的爱,对有点颓败的村庄的爱,对童年的全部怀念写在纸上。当我在回忆我的过去时,我似乎又回到了童年,看到了我提个竹篮子在村庄前后游荡,看到了在春天的田野里快乐地奔跑,追逐着翩翩起舞的蝴蝶,看到了我在有月亮的晚上坐在门槛上看远方的星星,星星那么亮那么亲切那么水灵,我的嘴角不知不觉露出了幸福的微笑。想到这一切,我似乎又度过了一个快乐纯真的童年。文字的力量就是那么大,让你在安静的思念中回到过去,回到那灿烂的岁月里去。 在琐碎的生活里,我也可以选择文学。生活里的点点滴滴,酸甜苦辣,悲与喜,泪与笑,苦与乐,复杂的人迹关系,狡诈、卑鄙、自私,人与人的内心的沟通,生活带来的一点点感受与思考,都能用文字一点一滴表达出来。很多次,当我把对身边人与事的种种看法用冗长的文字表述出来时,发现,禁锢我身心的枷锁没了,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走起路来也飘逸了,心情惬意了许多。这都是文字带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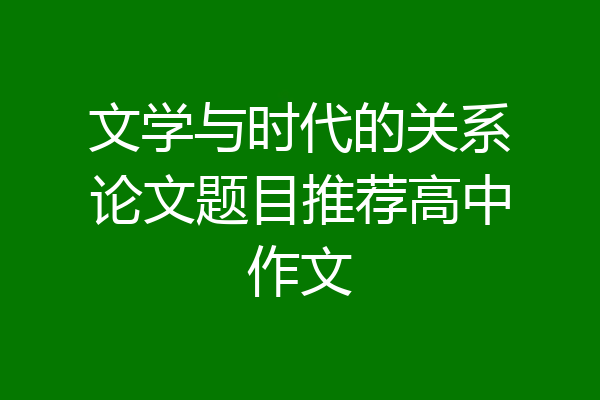
深秋过后,虽然没有下雪,但寒气却一天比一天的重起来。 这从玉京城里面家家户户屋檐下那一长溜,粗似儿臂,晶莹剔透,如刀剑一般锋利的冰棱就足可感觉到冬天的严酷了。 玉京是大乾王朝的都城。 大乾王朝鼎盛繁华,地大物博,辽阔宽广,人口数万万,是天朝上邦。 而今年正是立国六十年。定鼎天下一甲子! 这六十年,大乾王朝四代皇帝励精图治,已经到了一个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盛世。 “武温侯”府就在玉京城的东南面,占地百亩,地势开扬,大门口一对足足有三人高的红漆石雕麒麟,朱红大门,闪亮铜钉,铜环,门口衣衫鲜亮,中气十足,眼神锐利的家丁等等,都可以显示出武温侯的地位。 “武温侯”是大乾王朝的显赫人物,姓洪,名玄机。 此人不但爵位隆重,而且位极人臣,官居内阁大学士,太子太保。文武双全,年轻时能开九石强弓连射,骑大马冲杀数百人敌军如若闲庭信步。{大乾王朝一石是一百斤,九石相当于九百斤}。 二十二岁立下赫赫战功之后,又弃武习文,金榜题名,高中探花。授予官职,参与朝政。曾经得到过大乾王朝四代皇帝“上马能治军,下马能安民。”十字最高评价。 …………………………………………………………………………………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一大清早,在武温侯府邸的西北角偏僻小院落里面就传来了读书的声音。 洪易他打开一半窗户,在屋子里面生了一盆炭火,正在桌子边上读书,一副准备应付科考,揣摩经义的架势。 他身穿着青衫,眉清目秀,年纪在十五六岁之间,身体略微单薄。 房间里面很简陋,烧火的盆是铁盆,炭也是普通的炭,并不是侯门大户生火用的精致鼎脚铜盆,雕刻出各种野兽形状的“兽炭”。 他读书的时候,身边也没有书童,婢女研墨铺纸。这一切都显示出了洪易在侯府之中地位并不高,但却还有时间读书,不是那种奴仆之流。 “能不能为死去的母亲正名分,就看开春的恩科和秋天的会考了。先靠中举人,再中进士,金榜题名,加封三代…朝廷会下旨册封我母亲为夫人。母亲的坟就能牵进洪家的祖坟,灵位也能在祠堂中供奉着。” 洪易翻开一本书,读了两句,心中却想起了自己在七岁那年死去的母亲。 洪易的母亲嫁给“武温侯”之前,是玉京城有名的才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诗词歌赋更是文采横溢,卖艺不卖身,和武温侯在一次堂会的时候,对唱诗文而认识,后来就嫁入了侯门。 说是才女,其实是青楼“贱籍”。加入豪门之后,地位非常之低。 更何况,洪易母亲在嫁入侯门的时候,武温侯已经有了正妻平妻,她是做为小妾的身份。 大乾王朝法律,一发妻,二平妻,四小妾。妾的地位非常之低,有些豪门贵族,士大夫之间,还互赠小妾以玩乐。 妾在吃饭的时候,都不能坐下,要和婢女一样站着。 洪易作为妾的儿子,根本没有继承爵位和家产的权利。唯一的出路,只有通过科举考出去。 洪易心中也很清楚,自己若是能考中进士,不但可以脱离这个侯府做官出人头地,最重要的是可以为母亲加个“夫人”的名分。 大乾王朝重科举,一旦金榜题名,则有可能加封三代。 “夫人”这个名分可不简单。现在侯府之中有三位夫人。这还是温武侯洪玄机屡立大功,朝廷特别的恩赐。 一般的豪门贵族之中,也只有发妻是“夫人”。 在达官显贵之中,朝廷赏赐家里妻子为夫人,可是莫大的恩荣,比加官进爵更为有恩德。 “若是我中了进士,我若是中了进士,朝廷会加封我母亲为夫人。到时候,不知道那位正房,赵夫人是个什么样的表情?” 洪易喃喃念了两句“赵夫人,赵夫人…”眼神里面闪烁出了恨意。 洪易永远也忘不了,自己七岁那年刚刚懂事的时候,侯府里面中秋赏月举行的宴会,济济一堂的时候,自己父亲和客人呤诗,就因为母亲对和了一句,立刻遭到正夫人的当众训斥,“举止轻佻,不守妇道,青楼习气不改。” 那天晚上回去之后,自己的母亲就气得血脉郁积,吐血伤身,两个月后就病死了。气死的时候,自己母亲才二十五岁。 “这次开春之后的考试,我都准备得差不多了,不过还是要揣摩揣摩。” 洪易心中想着,合上经义策论,翻开了一本《草堂笔记》。 这本书封皮很新,但是纸质很旧,显然是没有人看的老书。因为《草堂笔记》并不是读书人科考的经义,礼法,策论,而是属于荒诞不羁的神怪笔记。 读书人不说怪,力,乱,神。这种书,准备科考的人是不看的。 不过洪易看它,正是为了准备科考。 因为这本书,是前朝宰相李严的一本笔记,写的是妖魔鬼怪,道士神仙,才子佳人,女仙狐仙。 “这本草堂笔记虽然满篇都是讲神怪狐鬼,才子佳人和女仙,女狐,但其实每篇都是一个寓言,不愧是上一朝的宰相,李氏学派的创始人。” “现在李严虽然已经做古,但朝廷之中大部分科考出生的官员,都是他的门生,这次主持考试的主考官,也肯定是他李氏学派的人。好好揣摩这里面李严借助狐狸鬼怪而表达的寓言思想,迎合他门人的口味,必然能都高中。” “那些宗学的书生,就算是优秀的,也只知道死读书,却不知道人情练达即文章,你的卷子就算妙笔生花,和考官的学派不合节拍,也肯定会把你刷下来。” 考试之前,揣摩考官的学派,思想,喜好而做文章,那是极其重要的。洪易虽然年纪小,但心中却是雪亮。 “好一个天意即民意,原来还有这样的解释。” 洪易突然看到一则故事,细细读了一遍,惊讶起来。 故事是这样的: 民间一个媳妇和婆婆晚上睡觉的时候,墙壁突然倒塌了,媳妇睡在里面,死死的支撑起倒塌的墙壁,让婆婆逃出去,自己被压死了。媳妇死后,婆婆很伤心。于是村里的人都安慰她,说是做了个梦,梦见媳妇被上天封为了城隍神。 当时李严和一群士大夫议论这件事情,一群士大夫认为媳妇的孝行可佳,但是封神的那些语言,都是村夫野语。 但是李严却力排众议,说那个媳妇是封神了,因为圣贤书里面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认为那个媳妇成神了,也就是天意,那么她就成神了。 众士大夫都笑李严读书太迂了,但是李严说出了一番大道理来:“其实神不过是人的念头所化,庙宇里面的神佛,之所以能屡屡显灵,是因为承受了人们的香火供奉和信仰。本来这个世间是没有神的,信仰的人多了,人们的念头聚集起来,神佛就诞生了。要灭神佛也简单得很,只要拆毁它的庙宇,使人们不再信仰它,用香火供奉它,它久而久之,就自然的消失了。” 其中有士大夫点了点头,又问道:“拆毁神佛的庙宇,使人不再信仰它,那万一神佛报应下来呢?” 李严又道:“圣贤书说,正直聪明为神,读书人只要内心刚正,严明,念头就自然和神一样的强大,神佛又岂能报应你呢?” “读书人刚正严明,自身念头强大纯净,已经近乎道家中的阳神天仙了。比起那些不能显形,只能托梦,报应的阴神要强大得多。” 众士大夫听见李严侃侃而谈,都心生敬仰,于是问他道家修炼天仙阳神的道理。 李严道:“阴神能脱壳出游,人目不能见,无形无质,魂魄一团,只能依托外物显示灵异,而阳神则与生人无异,显化种种法相,飞天遁地,长生不朽。” 当众士大夫正要进一步发问的时候,李严却正色道:“读书人只谈民生朝政,仁义礼法,神鬼之事完全抛开,今天已经是过头了。” “神佛本来是没有的,是人的念头信仰所化生出来?书中所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意自我民意’,还有这样的解释?正直聪明为神?阴神阳神?” 洪易觉得耳目一新,这则故事好像是为他打开了神秘的大门。 砰砰砰! 正当洪易沉思的时候,突然门外传来了敲打的声音。 是有人敲门,但是声音很大,是用脚在踢。 洪易眉头一皱,起身打开了门。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 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一个复杂的多边关系,它包括了从生活到作家、从作家到文学文本。从文学文本到读者,再由读者进行反馈的双向过程。社会生活不可能直接产生文学,必须经过作家的中介,即由作家的创造才得以实现。在这里,作家也即创作主体是文学得以产生的中心环节。另一方面,作家创造出来的文学文本也只有通过读者的接受活动才得以成为审美对象,发挥其社会作用。 文学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正如毛泽东所说:文学“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这就不仅肯定了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反映社会生活,同时又强调了创作主体即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在反映生活过程中的重大作用。现实一经作为文学的反映对象,它就不再是独立于创作主体之外的纯粹客体,而是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地被主体所观照,所摄取,所发现,所加工和改造,从自然形态的东西变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处处打上主体的印记。文艺创作是一种主、客体融为一体的意义创造,作家笔下的现实决不仅仅是对生活现实的“复制”,而是体现了作家创作个性和审美态度的“第二自然”。如歌德说的艺术妙肖自然,而非摹仿自然,服从自然。又超越自然。以往的再现说基本上属于直观反映论,把作家的作用仅仅看成摹仿或镜子式的反映,把艺术看成是与现实同质的东西。而能动的反映论在肯定生活是创作源泉的前提下,强调创作是一项复杂的精神劳动,在这过程中,主体拥抱生活,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对象化,创造出既源于生活,又与生活异质的审美容体。黑格尔曾经指出:“艺术作品中形成内容核心的毕竟不是这些题材本身。而是艺术家主体方面的构思和创作加工所灌注的生气和灵魂,是反映在作品里的艺术家的心灵,这个心灵所提供的不仅是外在事物的复写.而是它自己和它的内心生活。”丁黑格尔认为“绘画的基本原则在于内在的主体性。”至于文学.它用的则是更为观念性的语言符号作为媒介,用语言来造型、叙述和抒发感情.这样.无论在其内容上和表现方式上,都为主体性原则所深深地侵人。 一定社会的精神生产是以这个社会的物质生产为基础的,文学的发生、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并与物质经济生产的发展基本相适应。 在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个部分中,文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宗教等都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部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学,是受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制约,或说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经济基础对文学的制约与决定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着文学的性质。这是说,一个社 会的经济基础是什么性质,那么,在这个社会基础上产生的文 学,就其总体而言,也将具有这种性质。不过,通常经济基础的 性质对文学性质的决定,要通过政治等意识形态的传递。因此, 这种决定作用,一般是间接的。其二,经济基础的演变制约着文 学的演变。这是说,文学不仅是适应着经济基础的要求而产生 的,而且要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的。不过,促进文学变化 与发展的因素有多种,经济基础是这多种因素中最根本的一种。 通过经济基础的变化对文学变化的制约,要通过多种中介因素的转换。然而,不管怎么说,文学的性质、变化与发展,归根结蒂 是要受经济基础的决定和制约的。 从文学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上看,它们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交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文学是在经济基础之上形成和发展起 来的,它要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和决定;另一方面文学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并具有相对独立性。 文学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大致上可以概括为三种情况:或者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与发展;或者对经济基础起作用;或者在破坏旧的经济基础的同时又促进新的经立和发展。 文学的相对独立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文学的变更通常并不和经济基础的变更同时发生。就是说,当经济基础发生变更时,旧经济基础之上的文学往往不会立即消亡,而会延续一个时期,通常要借助新的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新文学与之竞争,才能促使或加速它的消亡过程。而且即便旧文学从总体上退出历史舞台了,某些旧形式还会在新的经济基础上发挥着作用。其次,文学的发展有着自身的历史继承性。每一时代的文学,虽然都是适应着一定的社会发展或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的,但它一经产生,就会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材料,凝聚着一定的文学惯例和传统,从而影响着后代文学的发展。就是说,旧时代文学中富有思想和艺术价值的优秀作品仍然会在新的社会条件里流传下来,成为欣赏的对象和创新的前提。文学的发展除了受社会生活的制约外,还受它自身内部规律的规约,即在继承中革新。在延续中发展。再次,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之间还存在着不平衡现象。这种现象表现为如下两种情况:其一,从艺术形式来看,某种艺术形式的巨大成就,只可能出现在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上,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这种艺术形式反而会停滞或衰落。其二,从整个艺术领域来看,文学的高度发展有时不是出现在经济繁荣时期,而是出现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时期。 总括起来说,从文学艺术总的发展趋势、总的历史进程看,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是相平衡的,经济因素是制约文学发展的根本因素。但在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里,两者之间既有平衡的一面,又有不平衡的一面,因为文学的发展还要受到上层建筑其他因素的影响与文学自身规律的规约。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比较接近,因而对经济的作用较大较直接。在上层建筑各领域中,政治是最活跃的因素,起着主导作用。因此,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这种影响表现在:第一,政治影响着文学的性质和方向。经济基础的性质对文学性质的决定作用,通常要经过政治的中介作用。就是说,先是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政治的性质,再由政治的性质决定文学的性质。同时,政治还可以影响文学的方向。政治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势必会对文学的方向以有形或无形的影响,特别是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或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政治,这种影响尤大。第二,政治影响着文学的内容与风格。文学虽不一定直接表现政治的内容,但政治会作为一种文化环境或社会气候影响文学关心什么、反映什么,并使文学形成反映政治形势与时代精神的总体风格特征。如初、盛唐文学,因其政治相对清明,往往表现出积极进取、博大乐观的风格;而中、晚唐时期,因社会动荡,政治昏暗,文学则多表现人民的不满与反抗的内容,其风格转向怨怒哀伤。第三,政治影响着文学的繁荣或发展。统治阶级的文化制度与政策,乃至统治阶级中权威人物的艺术趣味与爱好,都会这样那样地影响文学创作,对文学的繁荣与发展起着或促进或阻碍作用。当然,文学也对政治发生影响,但一般情况下这种影响是较为间接的,而且文学要通过特有的审美方式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才能发挥这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