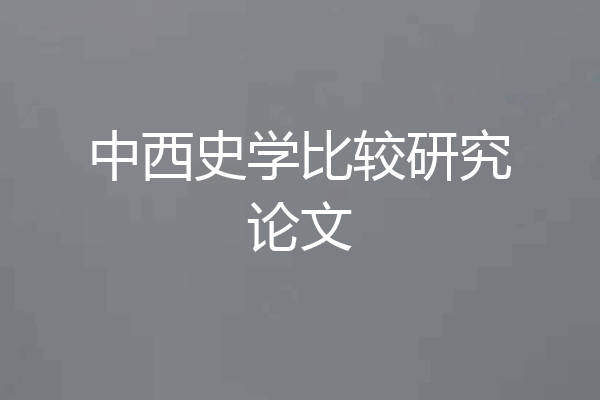陈龙cl
陈龙cl
谭桂林,湖南耒阳市人,1959年出生,199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师从国内著名学者王富仁先生,1996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此后一直在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现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现代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学术带头人,湖南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杂志主编,湖南省社会学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文学理论与批评协会副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青岛大学鲁迅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1996年被列入湖南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2004年被国家人事部评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从90年代初以来,谭桂林教授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跨学科比较研究,他是国内学界较早地深入探讨、综合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关系的学者之一,在这一领域中,他主持的课题有湖南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宗教文化复兴现象研究”等,出版的学术著作有《宗教与女性》(1995),《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1999),《人与神的对话》(2000),《百年文学与宗教》(2002)等。长篇论文《佛学与中国现代作家》发表后被《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全文译载,并获得中国社科院和共青团中央主办的首届全国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奖,《文学评论》1991—1996年优秀论文奖。专著《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被誉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填补空白之作,2002年获湖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3年获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这些研究成果也已经获得海外学者的好评,90年代末期应邀参加香港浸会大学第三届宗教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台湾佛光大学“海峡两岸当代禅学研讨会”。博士学位论文《佛学与人学的历史汇流》被收入台湾佛光文教基金会主编的《法藏文库—中国佛教学术论典》丛书。 二是现代中西诗学比较研究。在这一领域,谭桂林教授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诗学与西方诗学的关系研究》、湖南省教育厅十五重点项目《中国现代诗学研究》、湖南省教学改革重点项目《现代中外文学比较史》等课题的研究,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论文《西方影响与九叶诗人的新诗现代化构想》获得《文学评论》1997—2002优秀论文奖,是连续两次获得《文学评论》优秀论文奖的少数几位作者之一。另外,谭桂林教授还十分关注当代文学创作的现状与发展,运用文化分析与心理分析的方法对当代文学的一些重要现象进行综合与宏观的研究,近十年来,他主持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文化母题研究》,出版了《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谭桂林卷》(2000),《转型期中国审美文化批判》(2001),《长篇小说与文化母题》(2002)、《转型与整合——现代中国小说精神现象史》(2003)等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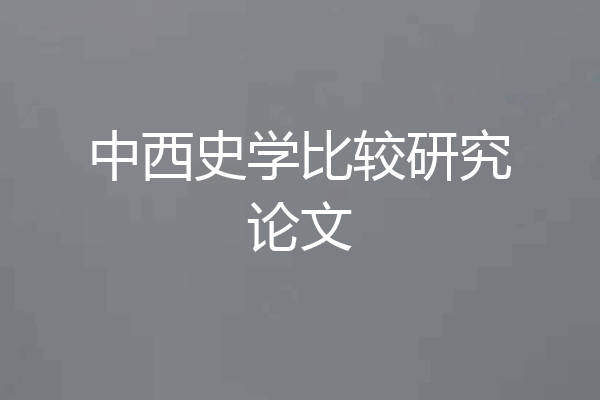
诗歌,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文学形式存在,无论在诗歌文化显赫的中国还是理性充斥的西方世界,诗歌在其文学领域都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今天,笔者将从诗学的角度解读中外诗歌。一般来说,诗的本体的确定总是要求建立起一种与之相应的诗化哲学。在西方现代诗人眼中,诗和哲学是相互贯通和相互联系的,它们同是人类精神的器官,同是认知世界的有效方式,因而,诗不仅不应拒斥理性和普遍性的概括,反而应在自己的大地上搭起一架神秘的云梯,接通理性的天国。于是,西方诗人普遍表现出强烈的哲学冲动。从波德莱尔开始,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大都较为重视理念等知性内涵在诗中的作用和地位。波德莱尔在《异教派》中强调指出:“任何拒绝和科学及哲学亲密同行的文学,都是杀人和自杀的文学。”艾略特对那种只会唤起读者情感的浪漫主义诗极为不满。他指出:“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所以他特别强调诗歌“非个人化”,即注重诗歌的客观性、普遍性与知性表现。在艾略特看来,诗人在创作中“知性越强就越好,知性越强他越可能有多方面的兴趣。”当我们在解读艾略特等现代西方诗人的这些对知性强调的论述时,我们一方面深深感到了知性对于诗与诗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艾略特等西方现代诗人的思维无论怎么变化,都没有超出西方传统诗学那根深蒂固的逻辑思维模式的制约。西方人那种喜欢按一种理性思辨方法去进行思维的意识已经化入了波德莱尔等人的骨髓里,使他们总想通过逻辑推理从杂乱的世界中把握出它的发展规律。理性就像上帝和灵魂一样,盘旋在西方的思维上空,散发着经久不息的科学的认知精神的光芒,它照亮的是诸如知性、理念、理智等诗学概念和范畴。与西方诗学重抽象的逻辑和系统的演绎推理不同,中国古典诗学以直观、领悟、体验为基本的思维方法。客观的说,中国古典诗学中不是没有形而上学的哲理,但这种形式上的存在从来就没有成为中国诗学家孜孜以求的对象。如道家的“道”,指涉的本是宇宙和生命的本体,但道家却并不对这个本体存在为何存在的形而上学理进行富有思辨性的考察。从根本上说,中国诗学感悟思维关心的不是某种终极价值的根据,或理性的认识结果,而是自我的内在情感体验。“诗言志”“诗缘情”论就充分的显现了这一诗学思维的非理性特点。不可否认,意象一直是中国古典诗学中一个核心性范畴。意象意境化,则被中国古典诗学视为诗歌意象的最高品格和诗歌审美的最高境界。在中国古典诗学这里,诗歌表现的意境不管怎样朦胧,它都是建构在人与自然和谐圆融的基础之上的。和谐性、静态性、审美性构成了中国古典意象意境化的诗学风格的本质特征。历史的车轮推进到20世纪初,中国古典诗学的意象观和意象体系受到了西方话语和时代潮流不可阻挡的冲击。象征性意象取代意境化意象成为了现代诗学中意象的最高品格,与此相关,矛盾性、动态性、审丑性的意象也取代了和谐性、静态性、审美性意象而成为了现代诗学中的主要审美构成和结构方式,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诗学风格由朦胧向晦涩的转化。这种由追求意象的意境化到追求意象的象征化导致的诗学风格的晦涩,从更为宏阔的背景上看,一方面源于诗人立足在一切都裂变成了碎片的现代沙漠中,已经不再相信古典诗学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圆融的乌托邦之境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西方的话语有关。西方现代主义诗人认为,现实世界和自然世界都是不真实和丑恶的,唯一真实的只有人的内在世界。而要表现人的隐秘的内在世界,就不能不用隐秘的、晦涩的象征和暗示。因为只有隐秘、晦涩的象征才具有一种暗示的神力,才能最为深刻的表现人的内心深处那些可见而不可见,可感而不可感的情绪波动和千回百转、转瞬即逝的欲望。中国的诗歌越来越西化,逐渐注入了理性的血液。中国现代诗学的独立发展与构建,基于中国古典诗学的厚重内涵和西方话语的引入与创造性接受,在坚持了独立、自由精神的同时,扩展了中国诗学的视野,开创世界性与民族性为一体的诗学体系与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