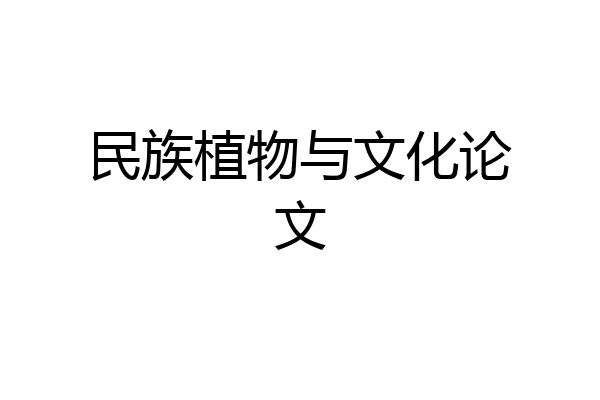michelhj
michelhj
傣族广泛人工种植的薪炭林树种“铁刀木”,是一种独特的人工薪炭林。在我国的56个民族中,西双版纳的傣族是传统栽培薪炭林的唯一民族。傣族聚居于热带森林茂密的地区,天然林可以提供大量的木材作燃料。但是他们从不砍伐森林取薪材,而发展了一种叫做“铁刀木”的人工薪炭林技术。铁刀木原产于泰国,引入西双版纳至少已有四百年以上的历史,作为一项薪炭林种植技术,已经遍及西双版纳海拔一千米以下的每一个傣族村寨,是傣族人民居家生活的主要能源。由于铁刀木生长迅速,不费管理工时,萌发力强,木材燃烧性能良好,当地人口平均每年消耗仅1~5立方米木材,每人种植面积只需5亩左右即足够轮伐利用。这一传统栽培技术不仅充分利用了这种树木的生物学特性和生态学特性,而且在经济上十分合算,并对当地热带森林的保护十分有益。从民族植物学的观点来看,人工栽培铁刀木在傣族传统文化中的发生、发展和普遍应用,可视为热带地区从事定耕农业的民族对湿热带生态适应的一个良好例证,在民族文化和生产实践上都有一定的意义。西双版纳傣族的“神山”(Nong)是一种原始宗教——多神教的遗迹,至今仍然保留于民间的信仰系统之中。傣族把自己村寨附近的一处热带原始森林,信俸为“神山”,即“神居住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动植物都是“神的家园”里的生灵,是“神”的伴侣,不能侵犯,应当爱护和崇拜,以求得“神”的保护,消灾免难,保障家园平安和康宁,因此,居民们每年定期举行“神山”的祭神仪式,十分虔诚。这种表面上看来是一种自然崇拜的迷信习俗,却包含着深刻的早期人类生态学观念。他们崇拜大自然的产物,而借助“神”的力量去保护人们的平安和健康,以求得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一致,是人类早期阶段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产物。当然,由于这种信仰本身不是科学的产生,往往为统治者所利用,成为他们巩固统治地位的一种信仰力量。但是,从研究这一传统信仰对森林植被的作用而言,却达到了保护森林的效果。西双版纳境内“神山”总数约400余处,估计面积为30000~50000公顷,目前许多保存完好的热带森林都是“神山”。西双版纳的傣族、布朗族都是信奉小乘佛教的民族。小乘佛教又称上座部佛教,约在唐代中期至下四世纪初期间,白缅甸或泰国传人。按该教教规,建立一座佛寺寺院,必须有四项基本内容:(1)释迦牟尼塑像;(2)一座佛塔;(3)不少于5名僧侣;(4)若干种特定的寺院栽培植物。按照僧侣对这些寺院栽培植物所作的解释,栽培这些植物于佛寺寺院之中包含三种不同的类别和目的,一是佛教礼仪植物,如贝叶棕、菩提树、高榕树等都是“佛树”,只能种于佛寺内及近旁;二是果树,如椰子、菠萝蜜、牛心果、绣球果等;三是观赏绿化环境植物,如鸡蛋花、睡莲、文珠兰、蜘蛛兰等。初步调查表明,共有58种寺院栽培植物常见于这一地区。这些植物的传播肯定与早期宗教传播有关,通过对这些植物的引种交流历史分析,可以认为历史上曾经有一条传播栽培植物的道路存在于我国这一地区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小乘佛教的信仰是这些植物传播的重要媒介。根据对西双版纳傣族、哈尼族、基诺族等少数民族植物学调查,科学工作者发现当地少数民族利用的植物极其丰富多样,他们利用植物于食物、穿衣、草药、盖房、编织、装饰、观赏、狩猎、捕渔、驱虫、祭祀、民歌民谣、民间故事、节日活动、传递信息、表达情感等。例如傣族民间草药达300余种,野生蔬菜120余种,野生食用果类100余种,野生香料40余种,野生用材树种76种,与宗教有关植物58种。他们采集各类野生植物,人工或半人工栽培有经济价值的植物,人工或半人工栽培有经济价值的植物,其中仅在傣族村寨家庭小园圃中栽培的就有280余种。他们把多余的植物产品拿到当地市场上出售或以物易物,交换他们短缺的生产、生活必需品。根据对当地集市植物产品的初步调查,这一地区常见的集市植物达170种之多。许多植物在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例如,西双版纳的傣族十分喜爱黄美花、香露兜等热带花卉,傣族妇女常以这些花朵为头饰物品;山地少数民族普遍流行耳饰,不同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的人群,常佩戴不同的植物为耳饰,以示区别,年青的未婚男女,喜欢佩戴一种叫“刺蕊草”的植物于耳部,西双版纳少数民族对植物的经济利用、文化利用和生态利用的知识是如此的丰富,为民族植物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所。云南少数民族中还有许多有关植物的神秘传说,例如,在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一带流传着一种神秘的植物叫蚱玛莲,传说此种草药消炎镇痛力极强,有“起死回生”之效,在旧社会为土司山官所控制,凡百姓发现此草必须送交土司头人,在外地市场上出售价格昂贵,常常以金相换。又如傣族十分迷信于“神树”,对此,科学家尚不能确切地加以解释,植物学和木材学鉴定并未发现任何奇异的特性,暂作“迷信”对待。这些源出民间经验的“迷”,只有通过科学的研究和检验才能作出真实可靠的解释。我国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如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朝鲜族、壮族、瑶族、黎族、高山族等,都拥有各自的利用植物的丰富经验和独特文化。生活在草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十分懂得草原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非生物要素之间的辨证统一关系。他们的传统草原生态学知识对于草原地区的生态平衡建设是十分有用的。但目前对于这些民族的植物学知识,还很少进行研究。 我国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工作然起步较迟,但是前景十分美好。我国悠久的历史,多民族的文化,丰富多样的植物资源,是开展这一领域研究的肥沃土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潮流,是推动这一学科发展的强大动力,党的民族政策和我国各族人民之间亲密无半的团结合作精神,是我国开展民族植物学研究的独特优势。可以预料,具有我国特色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工作,一定能够获得迅速的发展,使我国跻身于世界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先进行列之中。[以上资料暂时转自百度知道,裴盛基先生所整理,其他以后会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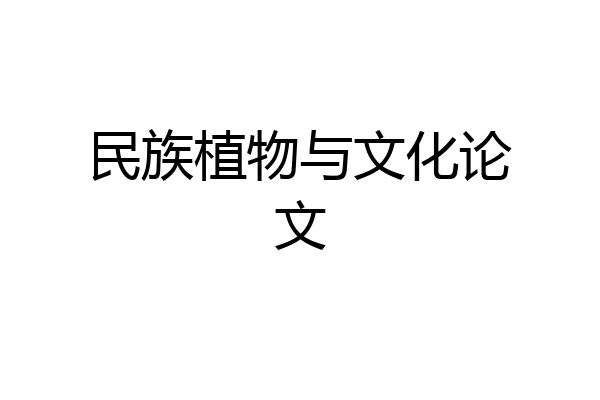
如何从花卉文化看民俗文化传承民俗文化传承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民俗文化是多姿多彩的。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同化下,在旅游活动的负面影响下,民俗文化的纯净性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为了使多样的民俗文化传承下去,必须对民俗文化的文化内涵进行发掘及宣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常重视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年11月2日第二十次全体会议根据IV委员会的报告通过决议)指出:“人类的共同遗产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的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利益予以承认和确定。”而各国民俗文化的多样性正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反映。民俗及民间风俗,是广大民众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现象,具有民族性与地方性的特征。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这些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反映了不同民族、地区的历史发展轨迹,也是一个地区或民族文化不断发展创新的根源。但在经济全球化、旅游活动日益频繁的今天,民俗文化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如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已不再愿意穿着本民族的服饰;按古规,苗族的芦笙在每年春种秋收这一段农忙日子里是不能吹奏的,可在贵州雷山县的一个苗族村寨,倘若来了旅游团队,不论什么季节,只要付上300元左右的人民币,就可以观赏到全套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