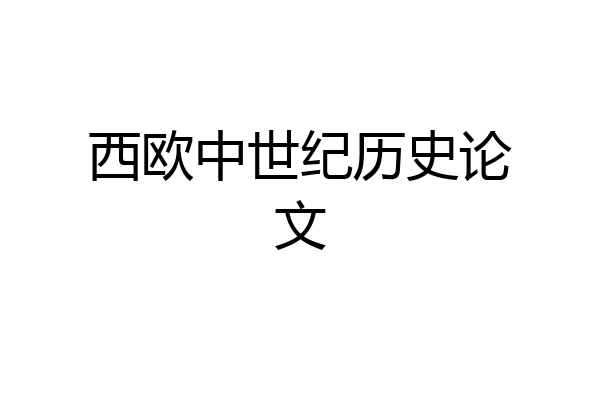潮解_ck
潮解_ck
提起中世纪的欧洲,尤其是西欧,对欧洲史略微了解一些的朋友脑海里的第一印象大概就是宗教势力,也就是基督教势力的权势熏天。的确,自从罗马帝国建立和巩固其政权后,基督教作为其压制人民思想、巩固政权统治的工具,越来越与世俗政权紧密结合,从思想上麻醉人民、从政治上钳制人民、从经济上压榨人民。中世纪的西欧经济发展缓慢,文化陷于停顿,这与基督教的精神统治关系极大。 然而,就像黑暗总是出现在黎明前一样,经过了若干个世纪的艰难的世事变迁,欧洲,尤其是西欧最终走出了中世纪各种因素的羁绊,迎来了其令后世无数学者和史学者仍对其原因探求不已的飞速发展时期。 那么,迈过中世纪这道门槛的西欧,其发展状况和其带给我们的历史经验教训又有哪些呢? 突破中世纪桎梏的历史标志性事件应该就是举世闻名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世纪的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在多种条件的促生下,于欧洲的意大利首先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为这场思想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可能。城市经济的繁荣,使事业成功财富巨大的富商、作坊主和银行家等更加相信个人的价值和力量,更加充满创新进取、冒险求胜的精神,多才多艺、高雅博学之士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这为文艺复兴的发生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和适宜的社会环境。 14世纪末,由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的入侵,东罗马的许多学者,带着大批的古希腊和罗马的艺术珍品和文学、历史、哲学等书籍,纷纷逃往西欧避难。(亦有一说是十字军3次东征(尽管第三次半途而废)带回来的纪念品,他们在路上发现了这些书,就搬了回来藏在教堂的地下室,后被人发现,惊叹古罗马的艺术,文学等,就开始极力传播,意图达到古罗马那时的成就)一些东罗马的学者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办了一所叫“希腊学院”的学校,讲授希腊辉煌的历史文明和文化等。这种辉煌的成绩与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人们追求的精神境界是一致的。于是,许多西欧的学者要求恢复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和艺术。这种要求就像春风,慢慢吹遍整个西欧。文艺复兴运动由此兴起。 在文艺复兴的背景下,西欧在文学、美术、自然科学、航海和建筑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西欧也以此为契机,从此大踏步地向资本主义时期迈进。并在此之后,凭借其制度上和经济技术上的巨大优势,领先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并把这种领先的程度一路保持到近现代。直到现在,西欧仍然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与西欧的文艺复兴有因和果的关系。 文艺复兴是一次逐渐发展的时期,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和事件。但文艺复兴使当时的人们思想发生了变化,导致了宗教改革和激烈的宗教战争。后来的启蒙运动以文艺复兴为自己的榜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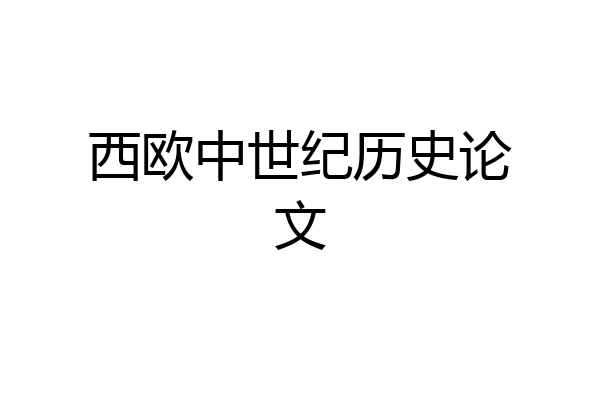
中世纪西欧的统一是文化上和宗教上的统一,在人们观念中的统一。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它形成了多元的政治秩序。与古希腊城邦时代相比,它的多元主义更加复杂多样,或者说,更加杂乱。 � 多元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教会与国家、教权与俗权的分化。它造成了西欧从社会权力结构到人的日常生活,从最高权力层面到基层的教区村镇、领地的最深刻的纵向分裂。有关政教二元化的问题将在后面详述。 � 在纯世俗政治领域,我们看到的同样是极其复杂的多元主义格局。 � 从水平方向上看,西欧并存着各种政治实体:帝国、王国、教皇国,以及多少具有独立地位的公国、伯爵领地、城市、主教领地、修道院等,每个政治实体都有特定的管辖权和管辖范围,其存在都有法律依据或历史根据,然而它们的权利和地位又常常相互重叠和冲突。在名义上,这些实体是属于不同层面的,帝国和罗马教廷属最高层面,[1]其次是王国,然后是公爵领地、伯爵领地、城市、主教领地、修道院等。但在事实上,这种层面的区分并不很清晰,且高一层面对低一层面的控制也是有限的,他们往往互不统属,各自独立。[2] � 中世纪西欧人在观念上笼罩在罗马帝国的巨大阴影之中。查理曼帝国和日尔曼人的神圣罗马帝国都被理解为罗马帝国的复活,在名义上,代表着西欧的统一。但查理曼帝国只是昙花一现,日尔曼罗马帝国只是徒具其名。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实现了对德意志王公和意大利有限的控制。天主教会是维护西欧统一的主要力量,它自身也具有统一的组织形式,享有对各国教会的控制权。然而它对各国教会的控制权也常常遭到蔑视。各国世俗政府控制本国教会的企图构成教会政治统一的主要障碍。各国的主教也有一种离心力,在教会利益与本国利益间常摇摆不定。 � 统一的基督教帝国的理想进入14世纪后就已经失去了实际政治影响,代之而起的是许多平等的主权国家并立的局面。不过,主权国家的形成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还在查理曼帝国解体后,就已形成了多国并立的分裂格局。每个国家发展起独立的个性。它们起初虽然权力有限,有的甚至极其分散,但它们是权力集中的焦点。在英国和法国,通过王权的加强,控制本国教会,将封建附庸转变为国王的官僚和臣民,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在德国,这种权力集中的倾向在诸侯的层面上表现出来,皇帝被架空,国家内部形成多元的政治实体。 � 各个王国虽然都具有向外扩张的冲动,但总的说来,扩张的意识并不很强,且总是被独立的努力和离心的倾向所抵销。并且,任何一个企图僭越的国家都会受到其它一些国家(或政治势力)联合的抵制与制裁。结果是在数百年之中,维持了一种“欧洲均势”。这种“均势”直到近代仍然如此。 � 从垂直的方向来看,西欧远没有形成统一的权力中心,更没有整齐划一的政治秩序。帝国与王国之间,领主与附庸之间,王国与城市之间、罗马教会与各国教会之间,都没有形成僵固不变的关系,更没有自上而下的绝对统治。每一种权力都受到来自水平方向或来自下层的权力的制约,每一种权力都由其它一些权力将其限制、阻挡和分散。上下之间保持着某种张力,但又不至完全破裂。整体保持着一定的内凝力,但又不排斥多样性和个体的独立性。到中世纪末期,这种不稳定平衡开始发生倾斜。在英法,迈向君主专制;在德意,则导致长期的分裂,集权过程在中间的层面上完成。结果是加剧了多元化局面。所以,中世纪西欧是罗马帝国大厦崩塌后散落的一堆碎片,是大大小小领地的连缀,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近代民族国家的三个要素:主权、人民、土地,在中世纪并不具备。国家没有最高主权,每块封地及封地上的人民可随领主的改变而转来转去。中世纪西欧人的心理特征在于,他们对这种“国将不国”、“天下大乱”的局面并未感到不安。 � 中世纪社会几乎所有的关系,权利、特权、义务、地位、身份,都是个别发展的产物,而不是统一法律和政令建立起来的统一制度。比如每个城市与其领主或国王的关系就是典型。每种制度都有例外,每个法律都不指望无差别地到处适用。所以,中世纪的政治制度是无法概括的,任何概括都易出现遗漏和片面性。 � 在多元主义的政治格局下,每个西欧人具有多重角色。分别与领主、国王、教会、城市等发生关系,被置于多重秩序之中。托马斯�6�1阿奎那曾谈到人受四重法律的支配,即永恒法(上帝的智慧)、自然法、人法、神法(教会法),[3] H伯尔曼通过对中世纪西方法制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法律所具有的独有特征在于,每个个人都生活在一种复合的法律体系之下,其中,每一种法律都治理个人作为其中一名成员的交迭重合的次级共同体中的一个。没有一种法律要求统揽整个司法管辖权。这些法律体系就是王室法、封建法、庄园法、商人法、教会法等。这样一来,各种权力体系汇集到他的身上,分割了他的生活。比如在中世纪英国,王权、教权和领主权汇集于基层,形成村镇、庄园和教区三位一体的社会组织。“在这种共同体里,教区执掌教化,村镇负责行政治安,庄园法庭管司法,三者独立行使职权。与此相应,生活在这种共同体内的每个成员既作为教区的教民,也作为国王的臣民,同时还作为领主的庄民。”[4]他使每个人的服从与忠诚并不固着于一个不变的权力中心。 � 在政治领域里,王室、贵族和教会形成鼎足而立的三大政治势力,他们的相互合作与角逐,是多元化政治秩序的典型表现。有时教会与王权结盟,神化王权,对抗贵族的分裂倾向;有时它又站在贵族营垒,联手扼制王权的专制倾向。在王权与教权的冲突中,贵族有时站在教会一边,抑制王权的膨张;有时又站在王权一边,抵档教权的扩张。王权同时实现对教会和贵族的控制在中世纪只是偶而出现过。 � 对西欧社会来说,多元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给社会带来混乱无序,甚至无政府状态。给人民生活带来无穷灾难和痛苦。然而它也产生了正面效应。它使任何一种权力无法实现对个人的绝对控制。各种权力彼此分割,互相竞争与制约,给个人留下了一定自主与自由的罅隙。 � 多元主义政治结构使每种社会政治力量都获得了存在的权利。在它们的互相竞争或争夺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每个国家(或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培育起了所谓“英国精神”、“法兰西精神”、“日尔曼精神”等,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和渗透,形成西欧多元化创造精神的源泉和多元化发展道路。法国是封建主义的典型,英国为西欧提供了大宪章和议会政治的范例。作为罗马文化故土的意大利率先兴起罗马法复兴的热潮,而瑞士州联邦则第一个建立了民主制度,给君主制的欧洲冲开了第一道口子。每一个国家选择了独特的道路,都为整个西欧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创造。各国发展的不平衡并没有导致一种力量长久占据优势,更没有窒息其它国家的发展。相反,各国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彼此消长,交错前进,推动着西欧整体的发展。 � 各种社会力量、各个社会等级、社会组织、团体和各种地域性的单位,教会、城市、贵族、僧团、行会、议会、修道院等,也同样发展起自己丰满的个性,成为不同创造力的源泉,为整体的发展做出了独有的贡献。[5]它们的相互竞争、激荡、渗透,使社会整体多彩多姿,充满生机和活力。同样,在思想领域,中世纪政治思想有多种源头:希腊的、罗马的、基督教的(官方的和异端的)、日尔曼的、城市的、伊斯兰教的、犹太教的等等。中世纪思想发展的一大奇观就是这些大不相同的文化因素的互相融合。 � 可见,中世纪的西欧呈现出没有秩序的秩序,没有中心的统一,混乱中的和谐。“伴随着这种混乱和骚动,我们看到对法治的坚定信仰,对正义的社会秩序的不懈追求:这就是中世纪政治制度史的真正特点。”[6]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欧中世纪的政治文化是不完善的,不成形的,或不成熟的。正因为如此,它也就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而不是凝固和僵化。没有一种理想真正实现,没有一种要求完全满足,创造与追求的冲动从未停歇。虽然从总体上说,西欧中世纪的发展水平是较低的,但是,它属于一种特别类型的文化,注定有远大前途。也就是说,只有这种类型的政治文化才能产生现代政治文明。并且,它有着惊人的发展速度。可以说,每过一个世纪西欧社会就有一种新面貌,变化往往是以世纪甚至年代来计量的。整个中世纪社会运动很像一场巨大的地壳变迁:经过动荡、破裂、组合、喷涌、聚积、沉淀,从未安静和停滞,不断有新的事务涌现,不断有蜕变与新生。从混沌的运动中,逐渐形成有序的新文明。到中世纪末期,它已显露出了基本轮廓。从发展水平上看,这时西方已经走在了世界各民族的前列。
欧洲自公元500年至公元1500年的一千年间被称为中世纪,这个时期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最为黑暗的时期。由于蛮族的入侵和定居引起了罗马帝国的崩溃,几乎造成当时欧洲文化的完全毁灭。西欧的封建制度便是在这一背景下,由日尔曼、罗马和基督教三种因素互相融合,从罗马灭亡后的废墟上产生、发展起来的。骑士制度同样也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是欧洲在封建化的过程中逐步产生、确立起来的封建附庸制度。中世纪的欧洲国家是一种松懈的领土集合体。在一个国家里,以皇帝、国王、公爵等为最高领主,其他大贵族则以向其宣誓效忠来换取封地——“采邑”,从而成为最高领主的附庸。这些附庸各自又可以拥有从属于自己的附庸,直到拥有少量土地或无地的骑士们,如此便构成了西欧完整的封建等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