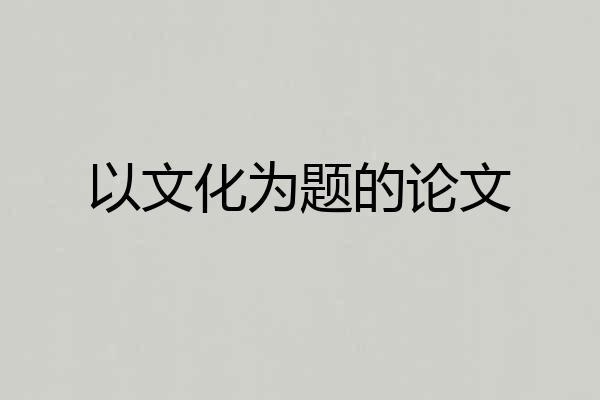地理科学酱
地理科学酱
浅说中国文化若说中国文化,只怕要从远古时期说起。但这一时期,一来离我们太远,二来我也不太清楚,便从封建时期说起。 许多讨论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都承认一桩事实:中国文化的基调是倾向于人间的,是关心人生,参与人生,反映人生的。我们的圣贤才智,历代著述,大多围绕一个主题,即治乱兴废与世道人心。无论是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汉魏各家的传经事业,韩欧柳苏的道德文章,程朱陆王的心性义理;无论是先民传唱的诗歌、戏曲,还是村里平淡的快板、小说,皆洋溢着强烈的平民特性,以及那无所不备的人伦大爱,同对平凡的留心与尊敬,对于千秋家国的情怀,对苍生万有的期待,激荡交融,缤纷灿烂地构造了平易近人,博大久远的中国文化品格。 然而前头还有一个“近代”。任何东西到了近代都很奇怪,文化也不例外。数不尽的冲击难以详述,单挑最惨的一回——五四运动。 之前已有“弃旧易新”的新文化运动将传统文化砍杀得飘摇欲坠,随后紧跟着爆发了五四运动,彻底树起了“白话文学”的大旗,文言最后成为一件历史文物躲进史书一隅供人瞻仰。 这两次运动大大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但在文化上却是严重的“左倾”。白话文学固然激发了俚语俗言的活力,提升了大众文学的地位和社会群体的文化参与力,却也设置了与文言文学不可逾越的天堑,几乎削去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力。老一辈学子影响尚轻,对于我们其误就越发明显了。以往属于孩童启蒙的“小学”教育,属于读书人必备的经学常识,都在新式教育的推动下,变得无比艰涩与隔阂,特别是近年来,电视、电脑等大众媒体的普遍流通,更造成了一个“畸形文化”当道、社会价值浮动的生活形态,使我们在现代化的整体架构上模糊了着力的点,漫漶了精神的面,却易于目迷五色地跌入学者所批评的“时尚文化”的辐射圈内,变得中不中,洋不洋。 余秋雨在《风雨天一阁》中写道:“只有文化,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此三言一语道破文化的本质作用,可谓精辟。中国文化历时五千载,到底何去何从,便不是我这个毛头小子可以阐述的了。 只好双手合十,默然祈祷,了我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对母语中文难以割舍的孺慕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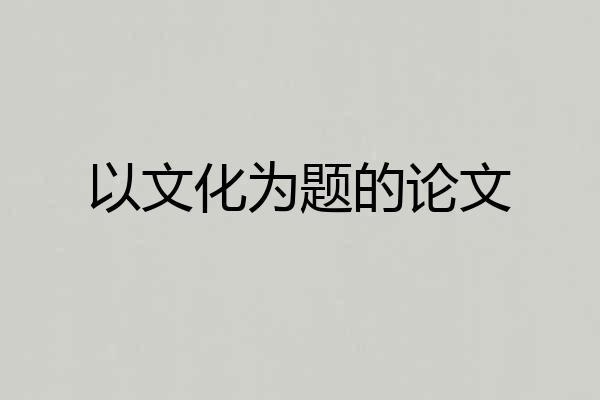
“文”的本义是“错画”, 也就是花纹。在古代汉语里,它的意义有所引申:因为花纹总是画在载体上的,所以,在人类认知领域里,“文”引申为后天加工的品德、修养,与表示先天素质的“质”相对。《论语.雍也》曾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是对处理好人的先天自然素质和后天人为修养的关系所发的议论。 “文”在政治领域里,引申为“文治教化”, 文治也就是礼治,主张利用礼乐教化提高人们的修养而使国家安定,与诉诸军事征服他国的“武功”相对。中国古代对“文”的认识还反映在对天文和人文的区分上:《易.贲卦》说:“圣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指的是自然现象和规律,人文指的是社会现象和规律。 “化”的本义是改易。这种改易既包括从无到有的“造化”,也包括宇宙生成以后的“演化”和“分化”。许慎《说文解字》的第一个字是“一”,解释说:“唯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这是中国古代的宇宙发生说,“造分”与“化成”,就是造化。在宇宙发生之后的变化中,又分自然之演化与人为之教化。医学著作《易·系词》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这里指的是自然的生成演化。《荀子.不苟》说:“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注释说:“化谓迁善也”,又说:“驯至于善谓之化”,这些指的都是教化。这一系列概念,反映出中国古代对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既统一又区分的观察方法。不过,在古代典籍里,化指教化的情况更多一些,《礼记·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这说明,中国古代观察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出发点是人文。 古人对文化的认识又是包含着新旧更代的运动观念的。《礼记.中庸》说:“诚则形,形则著,著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注:“动,动人心也;变,改恶为善也,变之久则化而性善也”,疏[1]:“初渐谓之变,变时新旧两体俱有,变尽旧体而有新体谓之化”,这里不但包含着运动变化的思想,而且还包含了量变到质变的思想。发生了质变才叫“化”。 在中国典籍中,“文化”很早就已合成——《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我们把“文”与“化”意义的内涵合成后,可以看出早期的文化含义。中国经典的“文化”是指人的后天修养与精神、物质的创造。修养属改造主观世界的范畴,创造属改造客观世界的范畴。 基于汉语“文化”概念的传统解释,学术界经常把它与英语的culture对译。Culture的原义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由于物质创造包含人的智慧,与精神文明难以截然划分开,因而与“文化”一词成为同义语。实际上,不经Culture转译的中国传统的“文化”概念所具有的后天创造演化观念和人文精神,更适合于今天文化学的文化内涵。